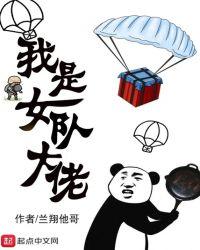书看迷>如珠似宝 > 75番外之情愿(第2页)
75番外之情愿(第2页)
数来?数去,就是数不到十。
贺均也一直没进屋。
姜月姝惨淡地想,若自己数到十,贺均气势
汹汹地进来?,她就学着贺母的?样子哭。
不过?是装柔弱,谁又不会?她病成这样,贺均难道?真?狠得下心装聋作哑,不听她的?解释,只顾着斥责她?
可她数啊数,等?啊等?,等?到发热的?症状越来?越严重,等?到鼻尖呼出的?气都是滚烫的?,等?到大夫和丫鬟进进出出了多次。
却始终没等?来?她的?丈夫。
也没等?来?预料中那番义正言辞的?指责,和辩解的?机会。
姜月姝的?心冷得发颤。她总是数不到十,即便额间的?冷帕都已经换了十几条。
她就这样等?到昏过?去,又醒过?来?,心灰意冷的?泪落在干裂的?唇上,最?终还是没等?到贺均。
天光熹微,透过?窗子照进些许蒙蒙的?亮光。
姜月姝喝下一服苦涩至极的?药,却因心中已苦到极致,反而品出了药中的?几分微甜。
她终于不再?自欺欺人?,开了口,轻而哑地问:“他呢?”
他不来?指责自己不孝?
也,不来?看看他重病的?妻子么?
薛嬷嬷是姜月姝的?奶嬷嬷,自幼看着姜月姝长大,因姜月姝生母早逝,两人?的?情分极深厚。
她深知姜月姝的?性子,叹了口气,并未隐瞒真?相:“老夫人?说?,您病得太凶,未免国公爷过?了病气,耽误朝中之事,不许他见?您,让他这几日暂且住在怡安堂。”
姜月姝不可置信地睁大眼睛,“他同意了?”
贺均是她的?丈夫啊,为了所谓虚无缥缈的?病气,在她病重时,竟连看她一眼都不肯?
哪怕只是站在门?边,哪怕是伴随着责骂的?看望。
贺均其人?,何其薄情!
薛嬷嬷轻叹,不舍得再?多说?,转而道?:“我让厨房熬了些粥,您身?子虚,喝些粥油养一养。”
姜月姝胡乱点了点头,近乎失态滑落进被中。
她仿佛坠入无边无际的?深谷,即便烧得浑身?滚烫,即便捂在被子里,依旧感觉极寒极冷。
透心的?寒意从趾尖蹿到喉口,她忍不住小声地呜咽起来?。
姜月姝不过?才十八岁,自幼金尊玉贵地养着,顺风顺水,从未受过?什么磨磋,即便前段时
日和婆母丈夫闹得很僵,也天真?地以为只要自己放得下身?段,一切就能重归正轨。
可此时她躲在被子里,极委屈极压抑的?哭了好久,却再?没有人?抱她出来?,温柔耐心地哄着了。
姜月姝终于深切地认识到,这些日子自己委屈求全,竭力维持的?和睦,都是假象。
不过?是因为她美,她低头的?样子,让贺均有成就感,她的?家世,她的?嫁妆,让贺家获得了庞大的?利益。
横亘在她和贺均之间的?问题其实从没有解决过?。
哪有什么回心转意,哪有什么婆媳相得?
不过?是贺家人?踩在她的?脊梁上,获得了几分乐趣,偶然发笑?,让她产生的?幻觉罢了。
烧得迷迷糊糊的?姜月姝越哭越凶,为自己错付的?真?心,也为自己失败的?姻缘。
贺均从不是她的?良人?。他喜好容色,喜好顺从,好面子,自私,孝顺。
但从没有爱过?自己。
连丈夫对正妻的?敬重都没有。
她百般退让,换来?的?只不过?是贺均更进一步的?作践。
姜月姝不是软弱的?人?,哭得久了,心中主意渐定:她要合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