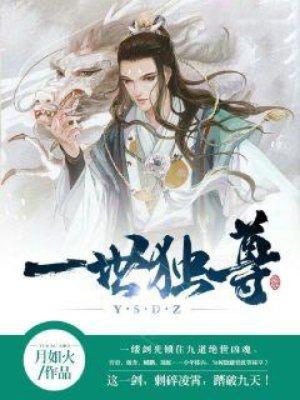书看迷>华木兰医仙 > 第2章(第2页)
第2章(第2页)
“是不是男子,找人一验便知!”
营地的女将们倒先不同意起来:
“你算什么东西?敢验我们的人!”
“就是就是,我看这老货就是存心,没事找事。”
副将又被我们气势唬住,那鼠眼男又一次出现在副将身边,再一次重复着那句话:
“是不是男子,一验便知。”
两个士兵正愈压我入营,“且慢!”
裨将气喘吁吁地上前,额头还挂着汗珠。
“副将如此污蔑我的兵,问过我的意见了吗?”
那副将依旧傲慢,甚至不愿多言。
“哪怕要验,也应该是我这个裨将去验,干副将你什么事?”
裨将将话又堵了回去,双方一下子爆发。裨将拎着我进了营帐,将我从上到下扒了个干净后,转而出营。
“本将验过了,是男子。”
那鼠目男还似乎有话要讲,却被裨将逼在了原地。
“怎么,你还不相信本将?”
“如果还有不服者,进营验证,如果是女子,我张赫尽提头负罪!”
“如果不是,请诸君提头见我!”
裨将狠狠地将剑摔在地上,一时间,营地寂静无声。
裨将再次对着副将说道:
“副将可要再验?”
那副将心虚地看了一眼营帐,转而悻悻地离开。
在场的女将无不松了一口气,我摸着头上豆大的汗珠,突然笑了。
这是我第一次,在这个世界笑。
除裨将外,营地里还有另外一个奇女子,她向来娇贵,多跑两步就会大汗淋漓。
活像个病弱小姐。
那小姐学得一手好医术,嘴巴却不饶人,除了裨将外,她谁也不服。
那日我拎着半条废臂找她医治,她没好气地看了我一眼,然后气呼呼地骂道,
“你怎么不死了再来?”
我一时被骂,只得悻悻地低头,烧酒洒在伤口上,一块烧红的匕首狠狠地戳进腐烂的肉里,我吃痛,倒吸一口凉气。
“疼就忍着!活该!”
我是她最不要命的病人,她总说在我身上操的心比当娘的还多。
“你是为何当兵?”
困意袭来,我们两个来守着营帐,闲聊两句。
“替父。”
“那你还挺牛,我啊,是不想听我娘的话嫁人。”
“我才不要嫁人,我学了十二年的医术,干嘛要在后院一辈子啊!”
“以后不乱了,我就在我喜欢的地方,建一个小医馆。”
“有钱的给几吊钱,没钱的送点吃食也可以,永州的大包子最好吃了,有机会我带你去吃。”
“喂喂喂,你理理我,别打瞌睡!”
谁也没想到,前日还对我们说话的裨将,今日已经孤零零地跪倒在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