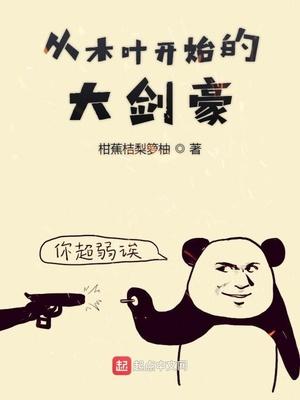书看迷>霸总O和金丝雀A > 第293章(第2页)
第293章(第2页)
徐乐颖在他面前站定时,温白后背已经冷汗如注了。
她质问:「你和简暮来接我?你要以什么身份?简暮的丈夫,还是普通朋友?」
没有开空调的客厅,在这滚热的夏夜之中气压低迷,如坠冰窖。
温白悬着的心终於死了。
「阿姨,我……」
「你们究竟是感情破裂,还是一开始就联起手来欺骗我?」
温白:「……」
他退,徐乐颖追,他插翅难飞。
温白想咆哮,简暮人呢,怎么就放他妈一个人出来咬人啊!
他和简暮本来就是各取所需,他需要一个向父亲证明自己不比任何人差劲的平台和跳板,正好还可以挡一挡父母那边的催婚,而简暮需要为他在陇峯中用身份地位镇压墙头草和敌营的人,同时需要为孩子找一个名正言顺的父亲。
他们一开始就是互利合作共贏的关係。
但这是能说的吗?
温白见鬼说鬼话,但他不擅长在长辈面前,特別是对着亲近的长辈撒谎。
他如鯁在喉的表情给了徐乐颖答案。
徐乐颖笑得讽刺:「果然在骗我,全都在骗我,全都把我当傻子。」
「阿姨……」饶是再巧舌如簧,温白也没有应对过这样的场合,特別是对象还是一个精神不稳定的半个疯子——在交心之后,简暮就把他家,包括他妈的情况都告诉他了,毕竟还要联起手来对付简鉞诚兄弟二人,总不能让温白什么都不知情就两眼一抹黑往前冲。
「既然什么关係都没有,你还来这里做什么?」徐乐颖骤然发难,她把温白往门口推,「你走,我不想再看到你,你也是骗子,你们全都是骗子,滚!」
大门砰一声砸在温白脸上。
-
再一次醒来,门仍然没有被打开。
大脑是这段时间以来前所未有的清明,似乎把这辈子的觉都睡清醒了,身体的潮热也已经褪去,原本仿佛被打断了全身骨头的钝痛也消失不见,除了后颈皮肉连带着腺体经久不散的疼痛外,简暮感觉自己好像重新变回了一个正常人。
从袋子里随便拿了个麵包,就着矿泉水囫圇吞咽,许久没有运作的咽喉和肠胃陡然受了刺激,简暮难受地咳嗽干呕,又被他生生忍住,艰难地咽下去。
靠在身后的纸箱上,趁着大脑仍然清醒,简暮目光放空,缓慢地梳理思绪。
毋庸置疑,他的身体肯定出问题了。
从发烧那天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