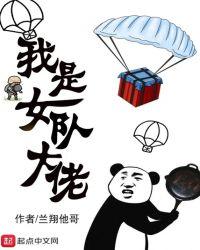书看迷>富贵田园妻 > 第27章(第1页)
第27章(第1页)
再看看一身的伤已被处理过,虽然还能感觉到疼痛,可是感觉已经好多了,应该能下床走走。
刚这么想,他双脚已落地,试着往前走了两步。
蓦地,他的笑容变大,身体的复原情形比想像中好很多,他以为会致残,或是留下永难治癒的痼疾,但是看来他是遇到不世神医了,伤得那么重也能妙手回春。
其实在他昏迷期间,罗琉玉又喂了他两滴灵液,她是嘴硬心软,受不得别人受苦,宁愿少喝几滴灵液,多积阴德。
“半壁兄,你好了呀!今日看起来气色不错,眼神也有神多了。”还以为不行了,没想到福泽深厚。
陆东承扛着一双儿女走过来,问候靠在窗边晒太阳的同窗,他脸上布满慈父的笑,对自家孩儿呵护有加。
“你是……呃,东承兄,你的胡子呢?”他记得这人原来是一脸落腮胡,活像打家劫舍的土匪。
他爽朗大笑,“被拙荆剃了,她嫌难看。”
远远传来虎啸声——
“谁是你拙荆,少往脸上贴金!”
他歉笑,但眼中可没有半点歉意,却有几分自得,“拙荆的脾气不太好,河东狮吼,还见谅。”
“又是虎又是狮,怎么不咬死你?”忿然的嘀咕声不轻不重,摆明是说给某人听。
不过各花入各人眼,有人爱牡丹真国色,有人偏好菊花淡雅,有人则爱闻梅扑鼻香,有人觉得兰中自有真君子。
“嫂夫人是性情中人。”夫妻俩的感情真好,叫一羡慕。
想到自己错过的那名女子,江半壁眼神黯然。
“她是不拘小节、为人率直,因为府中的一场变故,让她委屈甚多。”陆东承看向妻子的眼神满是柔情,也有一丝心疼。
“你是指朝廷以为你已死的事?”那时他还觉得可惜,陆家大房一门三父子竟一个也没留下,忠烈传家。
“还有我二叔,竟趁我下落不明之际,逼迫我妻子,想强行休弃她,以独占将军府。”
他一咳,“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只要你回来,以前的种种都会烟消云散,化做尘土。”
“这事谈何容易,皇上亲下的追封,若我没死岂不成了欺君,全府都得受到牵连。”皇上近年来反覆无常,益发多疑,杯弓蛇影。
“耐心点,总会有机会,不过……你那眉毛是怎么回事?”他掩嘴轻咳,不好笑出声。
“眉毛?”陆东承抖了抖眉,还在。
“你没发觉你一动就有白粉往下掉吗?”哎呀!太可笑了,看得他都想捧腹大笑。
“我脸上有粉?”陆东承动了动,果然有白色粉尘。
“咳、咳……下巴的泥巴干了……哈、哈……东承兄,请见谅,我真的忍不住……”
哎!他的伤口又疼了,可疼得厉害也止不住喉头的笑意一涌而出。
“什么泥巴?”他的脸上还有什么?
陆东承将两个孩子放下,走向井边打了一桶水上来,人俯向水面瞧,就看到一张柳叶弯弯眉的白脸。
“陈婉娘,你做了什么?”他黑着脸大吼。
“帮你改运。”笑得眉眼一弯的罗琉玉拿着早熟的甜瓜吃,还招呼孩子们来尝两口。
“你这叫改运?”把他弄成娘里娘气的模样。
“你印堂发黑,我帮你修修眉好开运,你这人业障很重,最好出家当和尚。”
“花和尚吗?”他冷笑。
“阿弥陀佛,满身罪孽,你快去刹度吧!”别老想重续旧缘。
陆东承泼水净面,洗去不该有的污秽,却没法让浓眉恢复,“婉娘,你我尘缘未了,你等着再为吾妻。”
“去挖耗子洞找老婆吧,恕不奉陪!”她一说完,甩头就走,带走两个玩累的小孩。
骑大马的年哥儿、莲姐儿真累了,一沾床就睡了。
“呵,东承兄真有福气,一双儿女养得玉人儿似的,粉嫩可爱,妻子也秀外慧中、落落大方,难怪你拚了命要回来,不忍放下他们。”那时他都放弃了,心想没有活路,唯有陆东承咬紧牙关,说有人等他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