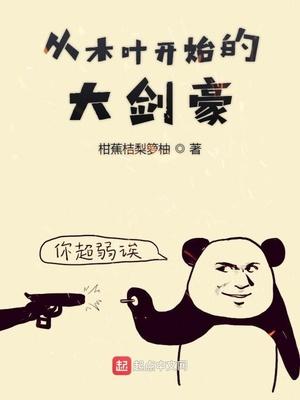书看迷>来自地府的公务员 > 第110章(第1页)
第110章(第1页)
慢慢地,两只眼睛的位置淌出鲜红的光流,混在白光里化为一幅幅发暗的老照片,掛在墙上。齐宣看见了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固定在黑白相片上,一男一女一孩童。
有人在说话,一张餐桌旁坐满了人,他们面容模糊,语焉不清。
只有迎春的脸清晰可见,她孤独地坐在桌子的角落,对面是个小男孩,正调皮地拿着塑料勺拨弄饭菜,扔得满座都是。
坐在男孩身旁的中年女人爱怜地帮男孩擦干净脸上的饭粒,笑着跟主位上的男人说着什么,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这时,坐在她身旁的老奶奶用筷子猛地敲在她手背上,口里骂道:&ldo;一家人说说笑笑的,就你成天黑着个脸,我们欠你的啊?
在她十六岁上高中那年,继母生下了弟弟。病房里,继母斜躺在父亲的怀里,轻轻哄着刚出生的弟弟:&ldo;现在孩子也有了,那个拖油瓶还继续养着么?
父亲的笑容僵在嘴角,含糊道:&ldo;你忘了那个和尚的话了?他说
迎春她妈妈一直不肯去投胎,要是我们对她不好,就会有报应。之前你流產那么多次,家里厂子破產,甚至我丟掉工作
也许都因为这个
继母看向怀里的幼子,眼中的慈爱更深,可嘴里说出的话分外冷漠:&ldo;那就去请一道符来,我就不信了,人还斗不过鬼!
她从高中就开始兼职,早晚只吃一个馒头就咸菜,中午去摊子上吃一碗一块五的炒麵,心里想继续熬着吧,到上了大学就好了。高三那年,她正在上课时,奶奶带着一群不认识的村里人闯进课堂,嚷着要带她回去结婚。
&ldo;我都说好了,女孩子念那么多书做什么?
她心里清楚,奶奶肯定收了人家的钱了。她求助於老师,求助於学校,最终申请到了贫困补助,並请来父亲带走了奶奶。她已经三年没见过父亲的面了,父亲仿佛又老了十岁,白髮苍苍,看着跟奶奶的年纪相差无几。
父亲说:&ldo;你安心考试,其他事我来处理。
这一瞬间,她特別想拉住父亲,问一问他有没有后悔过。
母亲‐‐他们好像都能见到母亲,可偏偏迎春见不到。奶奶说,要不是母亲作祟,早把她送人了,继母说,要不是母亲捣乱,她早生了三四个娃了
父亲从没说过母亲的事,他总是站在那里,看着他们,不说话。
时光流转,她独自一人站在人来人往的街道上,任凭阳光拉长了她的影子,又完全吞没。她身处黑暗中,抱着膝盖蹲在角落里,慢慢没了动静。
齐宣仿佛可以听见她的呼吸声,听见她小声啜泣的动静。黑暗中不断迴响着迎春的厉声尖叫,她在黑暗里不断撕扯着自己的头髮,自己的麵皮,自己的一切,她想要衝破这身皮囊,她想要自由。
奶奶说:&ldo;你也毕业了,別考什么研了,赶紧工作赚钱吧,家里供不起你。养了你这么多年,也是时候你出力照顾我了吧?
她点点头,成为这个家新的支柱。
&ldo;这个月工资怎么少了三百块?迟到?你起早点哪会迟到?我年纪大了能花你几个钱?我这都是帮你存着
她低垂着头站在那里,成年人的身体里住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头髮长长地垂在身前,挡住了脸上的泪水。柔和的夕阳从窗外照进来,她的影子被桌腿一切两半,歪斜着躺在那里,像一具扭曲的尸体。
耳朵里响起一阵吹拉弹唱,一群人聚在桌前吃饭,迎春身旁坐着个面容苍白的男人,他头上戴插红花的小帽,脸上掛着喜滋滋的笑容。迎春怔怔地看着面前的碗筷,仿佛想像到了它们摆在自己坟头上的模样。
男人站起来,拉着她的胳膊绕在自己的手臂上,两人交换杯盏喝下了原就属於自己的酒水。迎春嗓子眼里辣的犹如火烧,她咳得满脸通红,听见满座高朋笑得止不住。
她说:我不想结婚,不想跟那个人结婚。
奶奶冷笑着,把手里的锅铲一扔,丟在铁锅里发出刺耳的声音: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你还想攀上什么高枝儿?別以为上了个大学就能多卖点钱。他家出四十万,为的就是你这大学生的身份,別不知好歹。你以为你真的值这个钱?
她穿着一身红衣,衝破族人的包围逃了出去,她决心再也不回那个村子,再也不认这些家人。她松了口气,以为这下子终於可以得到自由
奶奶不知从哪里打听到了她工作的地方,拉了横幅骂她不孝,骂她嫁了人还不顾丈夫跑出来招摇过市
领导找她谈话,要么劝说奶奶停止这一切行为,要么,捲铺盖走人。
她想了许久,终於得出结论‐‐前者她办不到,后者,她从这里走了,又能去哪里呢?
她身上流着奶奶的血液,奶奶会像甩不掉的膏药一直贴在她身上,她们之间的联繫无法断绝,除非,死亡才能将她们彻底分开。
想到这里,她浑浑噩噩上了电梯,来到顶楼。最近有工人在楼顶安装太阳能板,所以门没锁。她趁着没人注意悄悄来到屋顶边缘,这里视野很好,她清楚地看到楼下奶奶拉起的那张横幅上写着的两个大字‐‐不孝。
她自小被教育要孝顺奶奶,孝顺父母
唯独忘记了她还有自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