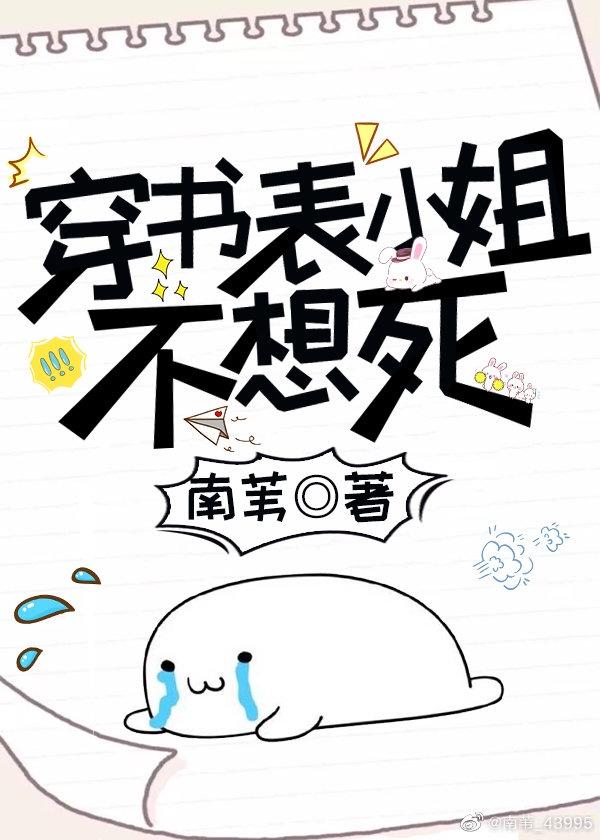书看迷>(综漫同人)退休魔法少女只想当一个称职的中原夫人 > 第149章(第1页)
第149章(第1页)
用肩膀顶开剧场的大门,全开的顶灯撒下格外通透的光,这大概是绮罗第一次见到如此明亮又空旷的剧场——平常排练的时候,通常都不会把所有的顶灯全部打开的。
舞台上已经搭建好了第一幕的所有场景,塞满了彩色纸屑的礼花炮也好好地安置在舞台上方的横梁上,就等待着在落幕的那一刻被拉响了。
深红色的帷幕被缓缓拉上。绮罗匆忙跑上舞台,从帷幕的缝隙间钻了过去,不忘与同事们道一声早安。
「布景都已经搞定了吗?」尽管是早就已经熟悉了的场景,她还是忍不住再次环顾欣赏,「还挺快的嘛。」
「昨天校工大叔帮忙把造景和道具从仓库搬到后台了。」
「是这样啊,确实是能省力不少呢。看来校工大叔的本体是田螺姑娘嘛。」
「虽然完全没办法把他和田螺姑娘联系起来,但再怎么说也该是田螺大叔吧。」
「那就是田螺大叔好了。」
绮罗笑着吐了吐舌头,不再继续开校工大叔的玩笑了。她拐进舞台后方的通道。
这段通道总是黑漆漆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能影响到舞台的效果,才一直都不开灯。今天借着整个剧院明亮的灯光,绮罗总算是能轻松地行走其中了。捧在怀中的两套戏服压得她的手臂都有点酸了,一走进后台的准备室,她就毫不犹豫地把这堆沉重的负担丢到了沙发上。
「早呀中原老师。咦,怎么带了两套戏服来呀?」小林说着,帮着一个同学拉上了连衣裙背后的拉链,「以防万一吗?」
「没错!果然还是小林老师最懂我了!」绮罗一本正经地冲她比了个大拇指,「总觉得还是做足所有的准备更好一点,否则要是突然出现意外情况,那可就糟糕了。」
虽然说得头头是道,但通常绮罗是想不到这种事情的。她想,说不定正是因为今天实在是起得太早了,才拥有了比平常更加清晰的思绪——并且也因此收获了双倍的疲惫,不过这可能要归咎于最近没怎么好好运动。
绮罗按摩着酸胀的手臂肌肉,不时转动一下肘关节,无聊地四下张望,意外发现班上的同学们居然都已经来得差不多了。
有几个同学聚在一起,小声地过着自己的台词。调皮的男孩子们拿着道具嬉笑追打,被老师嗬斥了好多次还是抑制不住好动的心,依旧闹哄哄的。也有坐在镜子前发呆的,不知道是不是在紧张着即将上台这回事。
总之,绮罗已经开始不争气地紧张起来了。
都到了这个紧要关头,居然还会感到紧张,实在是有点不像话了。身为这个房间里少数几个大人,绮罗知道自己可不能在小朋友们的面前展现出这丢人的一面。
她捧起戏服,磨磨蹭蹭地挪到了小林老师的身边,凑近耳旁,悄咪咪小声说:「那什么,我打算找个没人的小房间再突击猛背一下台词,这样可以吗?」
「为什么不可以呢?这种事也不需要取得我的许可呀。」小林老师对她笑了笑,「中原老师想做什么的话,去做就好了呀。」
「唔……好像确实是这个道理没错哦。」
绮罗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心想自己还真是提出了一个愚蠢的疑问。
重新捧起名为戏服的重负,绮罗在后台兜兜转转搜寻着合适自己的小角落,很顺利地一下子就找到了楼梯间下方的小仓库。
想来这里应该是平常不太会有人造访的地方,却意外的很干净。绮罗试探性地扌莫了扌莫堆在一起的纸箱,没有扌莫到任何一点灰尘。
难道说,这也是田螺大叔的功劳吗?
绮罗这么想着,把戏服从防尘套里拆了出来。既然仓库间也不脏,那就提前换上戏服好了。增加临场代入感,也是有助于记忆台词的重要方式之一。正好房间里有一根突出的横梁,她便把衣服挂了上去。
把纸箱作为桌子,又翻出了一个小板凳。绮罗卷起繁复的裙摆,随性地打了一个结。她该庆幸这不是容易留下折痕的布料,否则知世一定会伤心吧。
不过现在的绮罗可想不到这一层。她满心都扑在了剧本中,紧盯着纸上的每字每句,恨不得把它们都刻进自己的大脑里才好。
「你是什么人!怎么敢闯进……啊不对——怎么敢闯入尊贵的红皇后的花园里呢!」
绮罗小声念着台词。
没想到都已经到了这种时刻,她居然还是会犯错。虽说「闯进」和「闯入」不分,并非是什么要紧的大事,但如果一不小心嘴瓢了,说出了比这更加糟糕的重大失误,那不就完蛋了吗?
绮罗用力搓了搓脸,心想也许真该听从中也的建议,在手上打点小抄——也不是说把台词原模原样地全部誊到手上,只是写几个字或者是画几个图案用于提示而已,不至于会变成「幕后黑手」的。
绮罗悄悄动着这番「坏心思」,却差点被响起的电话铃吓到从小板凳上摔下来。
「呼……搞得好像我做贼心虚似的。」
明明她既没有开始打小抄,且这也不是什么「做贼」行为嘛。
电话铃声听起来好似分外遥远。绮罗想起来了,手机一直都放在外套的口袋里,并没有拿出来。
她站起身来,从头顶投下的白炽灯光被倏地扩大的影子盖住,视线也随之昏暗了一阵。
她迈出步伐,那一步却好像未能踩到地面。一阵急促的眩晕感冲上大脑。也许有那么短暂的几个瞬间意识断联了,周遭的一切飞速旋转,但实际在转动的应该只有她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