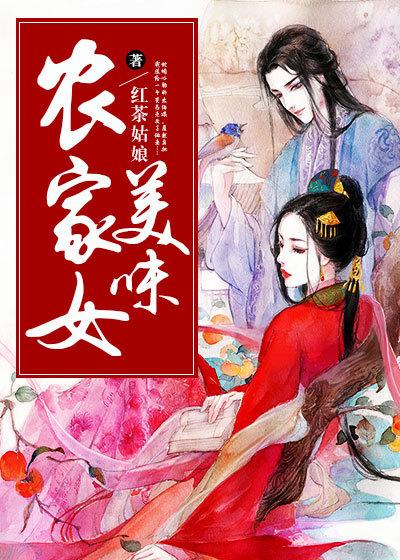书看迷>明月歌 > 120130(第16页)
120130(第16页)
她阖着眼睛躺在床上,听到他穿衣袍的簌簌声响,又听到他离去的脚步声。
以为他就?那样走了。
但过了一刻钟左右,他又折返回来,俯身在她颊边落下一吻。
凉凉的,淡淡的薄荷与清茶香气,又掺着几分?冬日梅香的幽静清冽。
这一回,他是真的走了。
沈玉娇抬起手,指尖轻触那清茶梅花吻过之处。
又要远行了。
她好?似也染上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毛病,想到上回裴瑕离家后的变故,一颗心也变得惴惴。
哪怕这府中如?今是她当家,仆妇、侍卫、武婢等人的身契都由她一手掌握,但裴瑕的远去,仍叫她心头缺了一块似的,空空落落。
于是她带着棣哥儿,暂时回了娘家住。
棣哥儿原本也很舍不得爹爹,但到底是小孩子心性,一到外?祖家,有阿瑜和阿瑾陪着玩,渐渐也将爹爹抛到了脑后。
倒是母亲李氏隔三差五就?在沈玉娇面前念叨:“守真也太实诚了,这样的苦差事,他如?何?就?领了呢?要我?说,称病也好?,辞官也好?,反正就?不该领。”
“那燕北是个什么地方,听说大冬日里,耳朵露在外?面,都能被冻掉!何?况那头还打着仗……”
“那些戎狄人都是茹毛饮血,丧心病狂的,若是与他们遇上……哎哟,阿弥陀佛。”
李氏想都不敢想,更不敢继续往下说,只?拽着自家女儿去大慈恩寺烧香拜佛,祈求着战事早日结束,女婿能平安归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长安也下了第一场雪。
这场雪落得比往年都早,仿佛预示着这个冬天将会格外?的严寒难熬。
起码沈玉娇的外?祖母罗氏没能熬过去。
老?太太是在梦里走的,走得很安详。
第二天早上婢女见她迟迟不起,一摸鼻子,才发现没气了,急忙去禀告当家夫人。
丧仪办得隆重,朝廷还下了旌表,以嘉老?太太此?生?忠孝节义?。
沈玉娇牵着棣哥儿去奔丧时,棣哥儿看着灵堂正中那个黑漆漆的棺材,有些害怕,直往她的怀里钻。
“阿娘,那个大盒子是什么?”
“那是……太祖母的床。”
“可是那床看起来一点都不舒服,太祖母为什么要睡在那里面?”
沈玉娇一双眼睛哭得有些红肿,低头摸了摸孩子的小脑袋:“因为太祖母要去很远的地方,只?有躺在这张床上,才能到达那个地方。”
棣哥儿正是对万物?都好?奇的年纪,问:“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比爹爹和谢伯伯去的燕北还要远吗?”
沈玉娇眼皮一跳。
没想到孩子会将这两件事类比。
当真是童言无忌。
她也不好?多说,只?道:“是比燕北还要远的地方,一个以后我?们都会去的地方。”
棣哥儿还要问。
沈玉娇止住他:“等丧仪过后,你回去问夫子。”
她这会儿正伤心着,实在没心情应付这求知欲旺盛的小家伙。
棣哥儿也看出自家阿娘眉眼间的疲色,乖乖闭上嘴。
当日夜里,沈玉娇准备入睡了。
棣哥儿抱着枕头来到她床前,黑黝黝大眼睛透着几分?难为情:“阿娘,我?能和你一块儿睡么?”
沈玉娇有些诧异。
毕竟打从这孩子落地后,他几乎都是由奶娘照顾,在隔壁房间住着。
裴瑕又夜夜与她同寝,自然也不方便让孩子与他们一同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