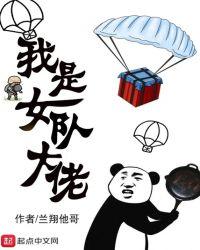书看迷>嫐(沟头堡的风花雪月) > 第8章 新4(第14页)
第8章 新4(第14页)
说到这儿,老男人叹了口气,拿起了一旁的汉白玉烟袋锅。
男人麻溜地把火给种了过去。
嘬了两口旱烟,老男人把眼一闭,似是不愿再提,“总归是被禽兽欺负了。”
烟雾缭绕之下,男人也给自己点了根三五,抽到一半时,还是没能忍住,“您别扔一只靴子啊,这不上不下的。”
老女人也叹了口气。随后,她说造孽啊,“幸好你爷还活着。”
中年男人问男人怎想起这段了。
男人拾起酒瓶给中年男人续满了,而后又给一旁的中年妇女意思一下,他说最近在看《大宅门》,想了解一下历史嘛。
“表嫂你再来点吧。”
给女人杯里续满之后,这才回到座上。
他看了看瓶中酒,对一旁的男人说咱爷俩把它分了,“老太爷跟老太就得了,不带他们玩。”
老男人磕抖烟袋锅时,男人已经半杯入肚,他说姥爷你还干哈呢,半天不言语了,“接着讲啊。”
老男人拾起杯子晃了晃。男人说你就守着吧,还惦着再喝?老男人说不喝了,喝也喝不过你,“你妈也不说跟着过来,就非得等过年才来?”
女人起身给老男人和老女人盛饭,她说四姑奶闲得住吗,一个人忙里忙外的。
男人也站起身来,他说我不就代表了,给老男人和老女人把汤盛在碗里,让老男人继续往下说。
老男人问说什么,后面还有什么可讲的呢。男人说故事总得有头有尾吧,哪能跳着来,“这可不是不尊敬人,也不是编造故事。”
“被折腾了一宿,人都没模样了……”老男人又叹了口气,他说吃斋念佛一辈子,没干过缺德事儿,怎就这个下场呢?
连说连摇头,“孩子最后打掉了,身子骨养了二年才缓过来,不是因为你爷岁数小,估摸早就不活了。”
他说很多事儿都成了禁忌,没人愿意开口再提,一是羞耻,二是伤疤,同时也会给子女心灵上造成伤害。
至于后来,他说内已经是二十多年后的事儿了,“孩子成家立业了,隔辈儿的也都拉扯起来了,该走就走了,解脱了也。”
送走中年男人两口子,男人告诉女人今儿先不去前院睡,“大表哥什么时候回来?”
女人说刚打白罗斯过境,再有个三五天就回来了,“在这儿多住几天,二舅妈三舅妈也该家来了。”
“不出五天姐俩就回来了,来前儿都告好我了。行啦,跟大鹏都回去吧,明儿我再前院跟你凑手。”
“把钱可准备好了。”
“你妈可真下得来茬啊大鹏,输我的五百到现在都不还,还让我预备?”
“表叔不有钱吗,可不就得宰你。”
“行,看到时我怎杀你妈的,连本带利收回来。”
空调外机上的雪化成水后没多久,院子里的花便含苞待放了。
当提箱被男人拉到院子里时,他也拍了拍狗头,还把手放到了狗鼻子上,像是要让二人记住自己身上的味道。
女人呵斥他,说狗没脸,说就记不住时,流转的杏核里一片瓦蓝,翘起来的小嘴都向上勾勒出一抹浅弧。
男人也勾起嘴角,而后笑着就跟女人一起上到了轿车里。
女人坐在副驾,和另外一个女人说笑着。
男人大马金刀地坐在后排,双眼一眯,透过夹缝扫视着前面二人,还哼了起来,“这一别,春风失意没知音,桃花含笑就上了祭台……”糟改着歌词,信手拈来,却也把前排二女逗得扑哧一声笑了起来。
台式机买回家后就接上了网线,女人说软件这块已然应用自如,只是打字始终还是二指禅地干活。
男人说这个好办,反正假期无事,正好教你。
于是年前大部分的时间男人都用在了教女人五笔输入法上。
有次女人终于忍无可忍,她说这还怎么学呢,心思都乱了。
男人说又没人催你,一次不行不还有二次。
女人眨起杏眸,说了句可别嫌烦,随后又说:“你在这儿搅合,我还怎练?”
男人嬉皮笑脸,还反问她烦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