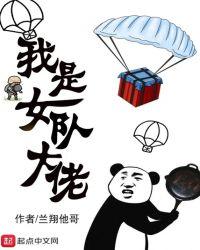书看迷>病美人剑修他声名狼藉 > 4964(第11页)
4964(第11页)
一派清和。
荡平魔谷,这本是一件值得称颂的功绩,然而因为做出此事的人是凌怀苏,性质就变了味。
世人不惜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他的动机,断定凌望此举是为了巩固自己千古魔君的地位。大概只有镜楚知道,斩魔物,平蛮荒,是凌怀苏幼时的志向。
没想到兜兜转转,自己成了最险恶的魔头。
魔气混沌浊重,污染心神,在所难免地勾起凌怀苏的戾气,时日一长,他肉眼可见地变得阴郁逼人,性情逐渐不可捉摸起来。
与镜楚的喜怒不形于色不同,镜楚是因天生灵物性情淡漠,鲜少有事能激起他强烈的情绪,而凌怀苏则是真的将情绪掩藏得极深,幽暗复杂的心思一砖一瓦,在肚子里筑起了深不可测的城府。
他依旧很爱笑,但笑眯眯的样子透着森然冷意,让人汗毛倒竖,仿佛下一秒便能将眼前人的头生生拧下来。
对于这个喜怒无常的魔头,有人恨不能啖其肉饮其血,得而杀之;有人见之胆颤,避而远之;而大多数人屈服于魔头的淫威,表面敬重,实则畏惧。
整座肃穆冷寂的不夜宫里,唯有镜楚敢招呼都不打地踏入露华浓,瞥一眼主位上的魔头,不满地数落一句:“怎么又瘦了。”
其实以镜楚的身份与能力,整日与一群魔物厮混在一起,是有些委屈的。
奈何他志向有限,只容得下凌怀苏一人。不论凌怀苏想做什么,他都会倾尽所能地支持,无怨无悔,誓死追随。
哪怕不为道义所容。
若凌怀苏追查摇光山一事,他便替他查;
若凌怀苏杀人放火,血洗仙门,他便带头冲锋陷阵;
若凌怀苏要当个名副其实的魔头,他便与他一同背负骂名。
毕竟摇光山覆灭后,能陪凌怀苏聊得上一两句旧事的,就只剩自己了。镜楚与他朝夕相伴,见过他不肯示人的脆弱,知道他难言的隐衷,无端油然而生出几分相依为命的责任感。
然而镜楚在心里兀自立好了豪言壮语,凌怀苏却不肯给他“誓死追随”的机会。
镜楚日渐感觉出,尽管凌怀苏待他如从前,两人还是微妙地生分了起来。
最直观的迹象,便是凌怀苏不再事事同他商议了。
这位新任魔君日理万机,开始不知缘由地消失,三天两头找不见人影。
某个夜晚,凌怀苏披星戴月地回到露华浓,疲惫地抬头,看见镜楚悄无声息地候在殿内,看上去等候已久。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幻境外的凌怀苏看了一会,才想起这是哪一天。
那时他受魔气影响,心性不受控制地日复一日暴戾起来,嗜血的冲动如附骨之疽般暗中滋长,他能清晰感觉到这种变化,却无能为力。
后来他找到了一种方法。
凌怀苏命人在后山湖泊上布了处淬骨洗髓阵,然后在夜深人静时,独自将自己关在阵中,亲手将祝邪捅进心口,待剧痛平息他沸反盈天的嗜血欲望,再将那些戾气尽数送入阵中。
如此,每次经历一番淬骨洗髓,至少能维持住一段时间的清醒。
那晚,他刚从阵中出来,回来时被镜楚逮了个正着。
凌怀苏脚步一顿,先是不易察觉地耸了耸鼻尖,确认身上血腥味已经被湖水洗净,才迟疑着走进殿内:“怎么在这”
镜楚看见他苍白的脸色,眉头一皱,伸手要来探他的脉,被凌怀苏不动声色地避开,若无其事地道:“有事要对我说么”
凌怀苏光顾着担心露馅,也就没注意到镜楚被他避开后一闪而过的神色。
而如今,那种失落的情绪通过心魔瘴,毫无保留地传给了凌怀苏。
镜楚盘问了凌怀苏这些时日的行程,直截了当地表示,以后有什么事可以交由他去做。凌怀苏自然听得懂他的意思,却都巧妙地搪塞过去。
后来两人心不在焉地各自聊了几句,直到更深露重,镜楚才离开。
凌怀苏记得,就在镜楚消失在殿门外的下一刻,他强撑多时的从容便再难以为继,虚脱地倒头昏睡不起。
那似乎是他们入了不夜宫后唯一一次促膝长谈,却都藏着话,你进我退,你退我进地旁敲侧击,顾左右而言他,在明里暗里的试探中渐行渐远。
凌怀苏知道镜楚察觉出自己的疏远,但他别无他法。
清醒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少,仙门正道的围剿一日比一日难缠,护魂灯的天山雪莲还未找够,罪魁祸首钟瓒还下落不明,妖族又时有暴乱……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完他该做的事,再最大限度地安排好后事,为镜楚留下一个清平人间。
然而好景不长,洗骨伐髓阵终究是治标不治本,用的日子久了,魔体似乎产生了抵抗性,理智维持的时间越来越短。
又一次险些失手杀了宫人后,凌怀苏意识到,不能再这么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