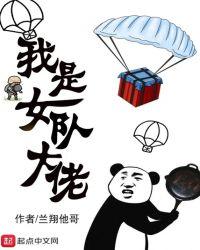书看迷>剑与她 > 第 3 章(第3页)
第 3 章(第3页)
白婳脸色微变,这才终于意识到,方才对他气势汹汹出手之人并非宁玦,而真正的宁公子,此刻就在她眼前。
怪她方才心神不宁,不然早该从言语中判断明晰。
宁玦没看白婳,只瞥了眼站在角落里大气不敢出的人牙子,说道:“买卖而已,你情我愿便成交,不成则一别两宽,何至于动手?”
臧凡收了镖,应付一句:“剑客游于江湖,随身丫头自要选胆子大些的,我不过试探一二,谁想她如此怯弱。”
宁玦偏过目,像是终于发觉屋内还有一人。
他视线落定在白婳因恐惧而略显苍白的面庞上,审视问道:“为何还不松手?”
白婳窘迫,反应过来立刻松开,又后退半步。
同时,脸膛不受控制得泛了红,虽是很浅的程度,但依旧没逃过宁玦的眼睛。
江湖上风风雨雨,打打杀杀的事儿见惯了,这种小女子的赧色……宁玦倒觉得十分新鲜。
臧凡方才没试出白婳的武功,一时只觉这女子伪装厉害,估计是个狠角色,自然不想留她在宁玦身边当祸患。
于是说道:“我不过试探,谁知刚一出手就把这丫头吓得软了腿,如此没有胆性,如何跟着你?走吧走吧,回去喝酒去,今天这批都不行,兄弟改天再给你物色别的丫头。”
臧凡说完,从怀里掏出些碎银子,扔给人牙子,给他当个辛苦跑腿费。
宁玦没有言语,见臧凡迈步,便也跟着要走。
白婳从失魂状态回过神,想起表哥的殷殷叮嘱,顿时鼓足勇气,硬着头皮开口争取。
“宁公子请留步!”她出声阻拦,解释说道,“我,我并非胆小,只是刚刚事发突然,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才会慌不择路。听闻公子居于岘阳山上,过着避世野居的闲适生活,如此,又何需身边丫鬟如打手一般胆大干练,体格强硕。阿芃愿跟随公子身边,尽忠尽力,照顾好公子的起居生活,只求公子能予我一安顿之所。”
声音娓娓,咬字温软,实在悦耳。
宁玦回首,眼前那张如花似玉,我见犹怜的娇靥竟明目张胆弯起唇,骋目流眄,浅浅对着他微笑。
一旁臧凡见状,戒备心想,好一出赤裸裸的美人计!
宁玦没有答复,白婳忍住心中惧意,抬头迎上对方的目光。
到此刻,她才敢去仔细瞧他。
宁公子身量优越,竟比表哥还要高些。五官没有不出挑的,俊美无俦,如画中人物,若非要捡出一处说,那便眼睛吧,剑眉星目,瞳眸深邃,眼底好像漾动着一池星河,熠熠明亮。
皮肤也白,与他身着的凡白色衣袍相映衬,整个人显得那么遗世独立。手执剑,剑鞘锈青发旧,虽握着武器,但周身气场并不锋锐刺人,不像时时经历刀风剑雨的江湖中人,倒是如同国子监里年轻的讲学先生一般,温隽和雅。
与表哥所形容的阴戾之徒,相差甚远。
不过很久以后,当白婳了解到宁玦真实的性子,才知今日对他的初印象是多么可笑又荒唐。
何谈温隽?他分明如虎狼!
人是臧凡寻来的,见宁玦不允不否,臧凡主动代替表态道:“姑娘请回吧,方才你没通过考验,更没达到我们的要求。”
宁玦像是默认了这个说法,面无表情从怀里掏出一锭银子,递给白婳,言简意赅道:“救急用。”
这是他进门后,对她说的第二句话。
白婳呆呆看着手里突然多出的银两,诧异于他的好心,一个凶恶之徒的好心。
只是手中银子的份量不过五十,她心头沉压的重石却足足重过千斤。
眼下恐怕是最后的争取机会,白婳焦急如受炙烤的蚂蚁,情急中,她蓦地想起表哥曾对她隐晦提起过,宁玦好女,贪色……
其面相并不像淫邪好色之徒,可白婳经历过家族落魄,体会过人情冷暖,早已看清人心叵测,更知得千人千面,人不可貌相的道理。
思及此,她心底冒出大胆试探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