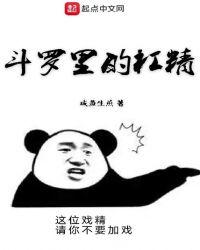书看迷>摧眉 > 返牢笼(第1页)
返牢笼(第1页)
江浔回了重越坊,不欲惊动邻里,悄声把门打开。
她收拾了银两放入细软,借着去木橱拿米粮的工夫,余光偷瞧院门,侍卫仍在马车上。
必是得了薛严吩咐,不能露面招摇,但侍卫也没有大意,仍掀开一道车帘张望。
江浔扭身,借视线死角将《鸳鸯姻缘传》藏于米缸内。这本书倘若随她带回刺史府,迟早有一天会被薛严发现,到那时后果不堪设想。
书放在这里,不会被他人轻易发现,说不定上官吾自己也能收回。虽说上官吾并不在意,可他还有白逸姐,不能不爱惜性命。
江浔把蔬果白米封口,都放到杜娘子家门前。这些日子多亏杜娘子照顾,数日街坊情意,无言尽在这一麻袋米粮之中。
回了马车,宁渊寻思江浔举动,分明不是位性冷心寒之人,偏偏对自家爷不假辞色,言语尖锐。
他好声劝道:“朔月姑娘,爷一直派人找你。昨日你出言不逊,以往按爷的脾气,你恐怕已身首异处,可现在仍锦衣玉食待你。你、你怎么就这般铁石心肠呢。”
江浔不自觉冷笑,世上岂有这样牛不喝水强按头的道理,她若是心狠,怎会又落得重回牢笼的下场。
她掩住唇角讥讽笑意,摇摇头:“你们主子侍卫一条心,一个立场,自然觉得我不识好歹。”
宁渊笨嘴拙舌,话头立刻噎住。以往看错了朔月,本以为温顺敦厚,哪想骨头竟比顽石还硬朗。他不敢多话,生怕话再听得多些,爷便又开始撒气,两头不讨好。
从后门回到薛严私宅,此时房内无人,两个丫鬟侍立门口。
江浔也不多问,自行解衣裹被睡下,渐入梦乡。
梦里似有声音传来:“江浔,论文格式错了,今晚之前改了重交。“是陶教授的声音,她急忙忙坐到电脑前,正要打开文档。
场景一转,江浔又回到了家里,爸妈在厨房忙碌,一家人在饭桌前其乐融融。她心里泛酸,喉头哽咽,待要上前拥抱。
忽然,眼前一切都飘散而去,薛严那张脸孔在她眼前不断放大、放大,狠声道:“你逃不掉了。”
她惊惶向前飞奔,一路黑不见底,浓雾笼罩,好像怎么也跑不到尽头。。。
薛严推门进来,便看到江浔睡不安稳,头左右摇动,脸侧流出细汗。走近一瞧才知,那不是汗,而是眼角滑落的泪痕。
平日心觉朔月如铜墙铁壁,看她梦中流露脆弱,薛严生出些许怜惜。寻思昨日欺压她太狠,以后得徐徐图之。他轻轻推醒江浔,江浔身子一颤,猛然坐起身,恍惚中不知身在何处。
脸旁有衣袖轻拂,原来是薛严给她擦去脸上斑驳。
她之前虽恨,可也没有梦醒后恨得彻底,只死咬牙强自忍耐。既然能逃一次,就有第二次,两次不行,就计划第三次。偏不信,即使自己逃到天南海北,薛严都能找到。
晚间吃了苏港厨子做的浇头细面,薛严给江浔套了一身黑色斗篷,乘船回往江宁。
有道是:水雾愁汽,衰灯船头啼寒素。黑垭暗海,孤影舱内怀悲眠。
船行一夜,在江宁烟淮驿停靠。
江浔身子单薄,抗了一夜水面寒气,加上心绪不佳,已是鼻塞脑涨。
薛严拿了羊绒毯细细围好江浔,抱着她上了马车。他低头看怀中人目含水光,粉帕掩住鼻头,分明是一副着寒极为难受,又暗自忍耐的模样,心头微动。
朔月平日再怎么刚强,终归是女子,吃软不吃硬。
他温言说道:“一会回府先让太医给你诊脉,你连喝了两碗避子汤,本就阴寒,此番受凉,当心伤了根本。”
江浔点头答允,要日久天长的耗着,当然不能跟自己身体过不去。
薛严一路抱着江浔往亭山院,江浔心觉难堪,埋首在他肩头。
薛严难得见她主动亲近,一怔,立即明白过来:“你怕什么,府内下人都经过调教,不敢偷窥主子私隐。”
江浔头脑发沉,听了薛严这话,更是心烦意乱,说道:“我脸皮薄,不想被人看到。”
这丫头又在反唇相讥自己脸皮厚了,薛严不欲和她计较,把江浔抱回善若堂。招来一个婢女吩咐道:“把朔月的细软都收拾出来,西偏房里的衣裳也放到爷这。”
他给江浔塞回被角,抚上发梢,语气平缓却不容置疑:“你以后就随爷住在善若堂,西偏房便留给你放话本。”
江浔知道多说无用,便出言答应。看粉蕊不在,问道:“粉蕊呢。”难不成打发走了?
提起这事,薛严又想起后墙的土包,面色不愉:“粉蕊身为婢女不尽其职,已被处置了。”
江浔气急,直起身道:“是我自己逃跑的,关她何事!你把粉蕊怎样了?”莫不是无辜丢了性命,念及这里,江浔不自觉身体颤抖。
“瞧你吓成这样,不过打了七棍略施惩戒。”薛严又按下江浔身子,怕激得她太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