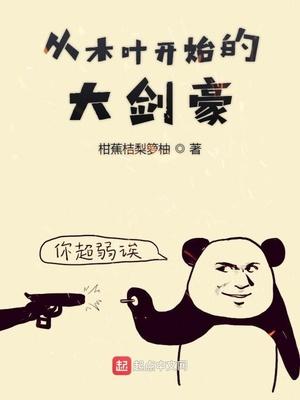书看迷>玲珑月 > past love(第7页)
past love(第7页)
金世安颠颠他的手,笑了。
这个冬天里,他两人并肩协力。金总是充分体会了产妇家属的心情,体会得太充分了,整整体会了三个月,真有孩子都能开幼儿园了,日日只恨不能脱胎换骨,赶紧重新生个露生出来。等到年初时节,叫了个德国大夫来——荷兰的没有,德国老头把露生检查了一遍,挑眉道:“现在只需要考虑健身问题了,他太瘦了。”
世安与露生相看一眼,都喜上眉梢。
健身方案就没什么可说的,德意志式的严格锻炼。金世安打算叫他起来晨跑,谁知太阳还没出来,就听人民艺术家在天井里吊嗓了。
金总在花架上托着下巴:“老子起得够早了,你他妈几点就起床?”
露生赶紧放下扳起来的腿:“我吵着你了?”
金世安笑了:“没有没有,挺好的,你这比晨跑还强,继续继续。”
露生有些局促,看他一眼,腼腆地背过身去。
“继续唱啊。”
“不唱了,你在这儿看着,怪难为情的。”
“那我不看不看。”金世安把眼睛蒙上,从指缝里露两个眼睛:“你看我蒙眼了!哎我说你以前不是专业唱戏吗?人山人海都见过了,凭什么老子不能看啊?”
露生不答他,半天从风里蚊子似的飘来一声:
“要你管。”
金总真心想笑,他拍拍屁股走了。走到屋里,又听见天井里明亮柔和的一缕清音:“春风拂面湖山翠,恰似天街着锦归——”
反反复复,只是这两句。那声音忽高忽低,是久病后中气不足的样子,可是柔婉清澈,仿佛唱出春光。
金世安不知道,那后一句没唱出来的,是花魁娇娇怯怯地一句念白:
“多谢了。”
朔风凛冽里,梅花也开了。
“去把帘子放下来,门关上,老子这个事情很秘密。”
露生迟疑了一瞬,有些怯意,又有些防备。
金世安“操”了一声,“大爷,我是很正经地要跟你说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不是要睡你,算了,我自己来吧。”
白小爷究竟是白小爷,金世安话里话外,激得他心下清明,他挣扎起来,关了门,放下帘子:“你说罢。”
金总看一眼露生满是防备的脸:“老子被你咬了一夜,你还让我跟你站着聊吗?”他拍拍枕头:“过来躺着说。”
原来金世安连着做了两个怪梦,总梦见回到2012年,自己在梦里身不由己,说话做事也是怪里怪气。他联想看过的爽文,忽然惊觉这可能是所谓的“对穿”,自己和金少爷都没有死,只是阴差阳错弄错了身体。
没猜错的话,现在的金少爷,正以海龙集团董事长的身份,逍遥快活地活在21世纪。
金总气得牙酸,牙酸也没办法,别人幸运a,被捅了还能少爷变总裁,自己他妈的幸运e,无辜被搞还要跟黛玉兽组队。
爽文只教会了他判断金手指(还判断错了),没教会他怎么回到原来的时空。金世安很想回去,也想夺回自己的身体,但做不到的事情不能干等,眼下当务之急,是在这个已知战乱的时代活下去。金少爷和自己互借身体,那么必然存在着不可断绝的联系。
这就是要挟白黛玉的最好筹码。
他试着把那条梦中的短信写出来————“秋光甚艷不知可有餘暇來敝處一敘”,又问露生,“你少爷爱喝的茶,是不是叶子很大,水也很绿,一根根竖着不怎么倒,像水草的感觉?”
露生喃喃道:“这是猴魁。”
又看金世安摹的短信,十来个字里倒有五个字写得不对,显然写字的人没读过几个书,但原笔措辞文雅,语气谦逊,尤其口角是他熟极了的,不是金少爷又是谁?
金世安把被挠成布条的衣服解开:“胸口的伤自己看,是不是你那天戳的?我知道这个说法真的很离奇,换我我也觉得太扯淡,所以信不信由你。”
露生木然无言。
穿越都有了,灵魂交换又有什么不能信呢?
金总看他表情有戏,立刻发散要挟:“你可以弄死我,或者叫金老太爷来搞我,不过我跟你保证,要是我死了,你少爷立马也得跪。”
“跪?”
“就是我死他也死,我活着他也活着,我们俩现在有命运的联系!”金世安装神弄鬼。
白小爷显然很捧场,白小爷立刻就有害怕的表情。
两人一个哄得毫无技术水平,另一个信得没有智力底线,凑在一起活像两个弱智,金总忽然尴尬地觉得,他们这组合别说解放中国了,很可能迈出榕庄街就要玩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