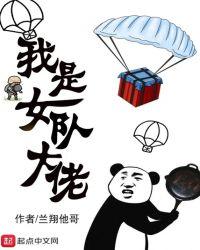书看迷>龙傲天的金手指是我前任 > 100 雪顶听钟七 她要纵身入(第1页)
100 雪顶听钟七 她要纵身入(第1页)
他说了那句话后,曲砚浓很久没说话。
牧山的风如此轻柔,吹得她身上云纱袖微微拂动,偶有一角浅浅地擦过他手背,又在风里一触即分,让人经不住怀疑那是不是他的一场错觉。
卫朝荣眼眸垂着,定定地望着他放在桌案上的那只手,看云纱袖在风里偶然飘起。
风很乱,衣袖摇摇晃晃如纷飞,有时向前,有时向后,在一千多次呼吸间,只短暂地奔向他一两次。
他默数一千次,只为那一两次。
“你这人真是怪。”曲砚浓终于开口,打破这长久的缄默,可她的声音听起来飘飘渺渺的,如隔云端,“有时候看起来也挺精明的,怎么总做傻事?”
卫朝荣沉默了一瞬,语气平淡冷冽,反问她,“什么算精明,什么又算傻?”
曲砚浓却像是被问住了,微妙地停顿,答不上来。
“你说我做傻事,你觉得我不该这么做。”卫朝荣语气寒峭而平稳,听起来并不咄咄逼人,言辞却堪称犀利锋锐,“你当然不会觉得你自己不值得,所以你是觉得你和我的这段露水姻缘不值得我这么做。”
卫朝荣抬眸,直直望进她眼底。
“可你既然觉得不值得,又为什么要来试?”他反问,连英挺眉目也凛冽迫人,极度锐利,“你知道不值得,为什么还要来试探我会不会犯傻?”
曲砚浓失语。
为什么?
她默然。
说来说去好像说不通,可归根结底,不就是她心里隐隐约约有期盼,希望他为她犯傻。
原来她心底已有几分相信他的情意深笃,不再是有所保留的露水情缘。
她的心已有了答案,到这个地步,还踌躇不前有什么意义呢?
曲砚浓抬起手,指尖在他面颊边轻轻点了一下。
如荷叶上的露水滴落湖面,很轻,却推开一重又一重涟漪。
卫朝荣一把握住了她的手腕,拇指按在她掌心,不轻不重,正好将她留下。
曲砚浓任由他攥着,什么话也没说,目光渺渺地望着他。
风月幽微,褪去针锋相对,她美得活色生香。
卫朝荣微微用力,将她拉向他,她像风中柳枝一摇即动,轻飘飘地靠在他怀里,坐在他腿上,抬手抚过他面颊,吻了他的唇。
他的手从她背后环住,深深拨入青丝,五指抵在她脑后,将这个吻推得更深。
最初,这个吻很静谧,她和他都深深克制,呼吸声轻轻浅浅,绵长而安谧,好似谁都很冷静,只是专注地将唇齿缠绵推深到最深。
可缠绵的呼吸一声又一声,渐渐的急促,彼此的脸颊滚烫,不分你我。
他的吻像炙热的潮水,涌过她唇齿、眉眼,涌过她的耳鬓,涌过她纤长的脖颈,无尽流淌。
她虚虚地搂着他的肩头,一点声音也没有,背脊挺得笔直,比谁都坚执板正一般,可浑身都在颤,竭尽全力才坐得直直的,一丝多余的力气也提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