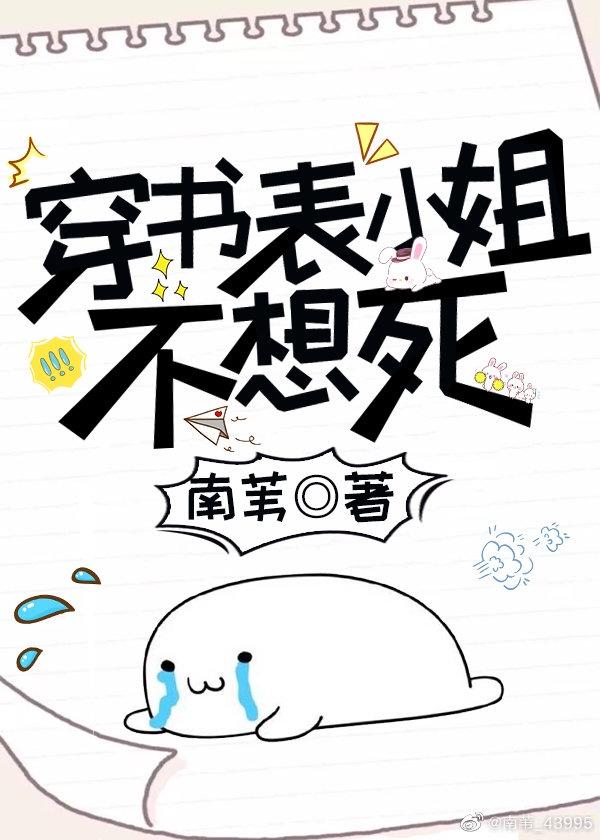书看迷>白月光分手日常 > 第560章 白茶清欢1(第6页)
第560章 白茶清欢1(第6页)
小郎君凭借着本能,贴着她的脸颊。
“班班,我们跟爹娘坦白吧,我要你,不要姓屠的,从出生到现在,除了爹娘,就你对我最好,让我最快活。我的田产铺子,我的衣裳饰物,我都给你,等我死了,你就为我守寡一年,期间多想想我,然后一年后,你风风光光再嫁,好不好?”
他难掩愧疚,“我不能火葬,我,我是个病秧子,无法在爹娘跟前尽孝,我的生前快意给了你,只能死后入了地宫棺椁守着他们了,你不要怪我,好么?”
他仰头亲她软颊。
她松口,“……也行!不火葬也好,日后我回来看你,还能亲你的骷髅架子!”
小郎君笑了起来。
少年还不曾这么活泼明媚地笑过,咧着嘴角,露出一口不太齐整、微微乱翘的小白牙。
“好!任你亲!”
俩人你一言我一语地商定日后。
般弱觉着他跑不掉了,是她的掌中小猎物了,痛快抱着他跳下了窗。
她脚步极快,到了河边,雇了一只小船。
那旧帘儿低低吊着,水波荡漾,舱内昏暗,横着一尾鲤鱼灯,她解开他的衣袍。白清欢好奇地低下头,尽管他看不见,还是努力地感知她。
其实也不用费力感知——
她分开他膝,动静大得吓人!
要、要被折断了。
白清欢吓得眼窝盈水,整条覆眼的缎帛都要湿掉。
“班班,班班……我有点……”
她又吻了过来,让他稀里糊涂地昏掉。
这一头小白雀养尊处优,囚在华贵的鸟笼里,不见天日多年,呆头呆脑的,没见过任何生人,怯生生得很。当它被捉在掌心,竟害怕得哭了出来,泪珠颗颗滴落。好在是被般弱温柔小意哄着,跌跌撞撞地昂起雀颈,边飞边哭,唳叫不断。
又顾忌着外头的人声鼎沸,他紧紧咬着唇。
“小梦,你怎么哪里都好看呀,浑身玉一样的,通透又白,真是美死了!哎呀,真想一口吃掉你呀!”
小妖精百无禁忌,说着没脸没皮的话儿,心满意足极了。
小白雀哭累之后,乖顺伏在她的手心。
白小梦心跳如擂鼓,有些不敢看她,怎么会这样呢,被她如此亲密抚摸,他非但没有缓解,好像病得更重了,全身都在烧着,是快要死了吧。
若死是这样的,倒也不怎么难受。
“哇!你看!好多花灯!”
她又被外头的热闹勾引住了,急急探出半边身子。
当然,般弱也不忘捎带她的病美人儿。
俩人顶着半弯的银芽月,就挤在窄窄一条小船里,胸膛半趴着,脸儿相贴,被照在绿波里,船边开着簇簇红莲,光璨璨的,热烈地燃着。
般弱牵他的手,去触碰沿途流走的水上灯。
尖尖的角儿,花蕊是滚烫的,这便是水上莲花么?
白清欢闭着眼,细致耐心触摸着这一盏盏微湿的浮灯,有的柔软,有的粗糙,唯一不变的是,莲心是热的,像她的手心,只要被牵着,哪怕是被绊倒,亦是很安心。
真好。
人间真好,有糖龟儿,有水浮灯,这么热闹,这么好玩。
他单是触碰着,就觉得胸口酣热到不行。
第一次,他想用力活下去,活得久一些,更久一些,让她留得久一些,不要急着改嫁。
般弱玩得正起劲儿,脸颊软软湿湿,小郎君也湿透了一条蒙眼的白绸,满河的花灯照得他长命锁澄澄亮亮的,唇珠同样嫣红美艳。
“班班,我会越长越好看的,做你天底下最欢喜的。”
“你若是中意小秃驴,我给你剃光头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