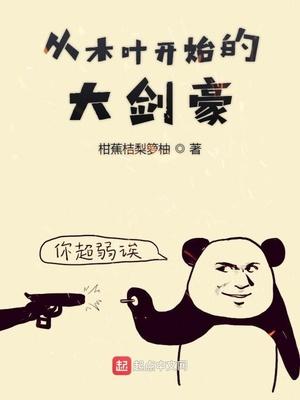书看迷>怪你风情惹火 > 第45章 第45章(第5页)
第45章 第45章(第5页)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门被推开。
云及月松开袋子,一脸生无可恋地半靠着门,丝绸睡裙无形间勾勒着曼妙的身影。
客厅里有暖气,她懒得披外套了。
但是她很快发现江祁景还没走。
云及月立刻站直,时刻警记着一个单身女性面对陌生男人的分寸感:“你怎么还站着不动?这是我的花园诶,你要是真的很想淋雨,能在我的花园之外找个空地吗?”
江祁景置若未闻,视线落在她腿边那一大袋东西里。
全部都是纸制品。
他的脑海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念头,心脏悄然揪起,呼吸声都变得急促:“那是什么?”
“我要扔的垃圾啊。”她弯下腰,根本提不起来重得要命的袋子,只能连拽带踹,动作格外简单粗暴。
过了一会儿,云及月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江祁景想问的不是这个。
她手指还拽着袋子,别过脸,有些尴尬地道:“就……我以前写给你的那些比较矫情的东西。”
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塑料袋上的两根细带因为承受不住,“啪”地一声断掉了,最表面上的几十封立刻滚下了台阶。
像是多骨诺米牌产生的连锁效应,整个袋子瞬间重心倾斜,所有东西都唰唰地往下掉。
有些直接掉到了台阶之下,有些被吹起来,飘进了草丛里,还有些被狂风卷得到处乱飞,也不知道归处在哪儿。
江祁景的心脏也跟着失了重,直直地往深渊里掉。
他大脑一片空白,根本来不及想其他,半跪下来,不顾形象地将那些散落的信封全都收集好。
不断有信封掉在眼前和周围,江祁景连忙一封一封地捡起来,手指将上面的污泥和褶皱抚平,紧紧攥进怀里,仿佛是拿着什么珍贵的宝物。
袖口早已经脏得一塌糊涂,连右手腕雪白的纱布都浸满了浊水,他却全然不在意。
像是疯了一样。
但是上百封散落在各处,他一个人这样胡乱地捡,一时半会根本捡不完。
目光所到之处,江祁景清晰地看见许多信封湿得近乎透明,仿佛已经被雨水冲刷得烂掉了。
他突然停止了动作。
只有手臂还在用力,紧紧搂住了怀里小心翼翼保护着、还算完好无损的幸存物。
雨在那时好像越下越大,雨水淌进心里,渗进裂缝中,滋生出锋利的尖刃,将血肉绞得支离破碎。
她有一点委屈。为什么在病房里云及月说好可以把这些情书送给他,现在又反了悔。
可是有什么东西比委屈更多,在心里疯狂滋长,变成粗粝的藤蔓,扫空了身体里每一个角落。。
那些情书在他面前,一点一点地烂掉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
什么都做不到。
做什么都是回天乏术。
江祁景又看见有一张没有信封的信纸,湿漉漉地躺在水洼里。
信纸的第一行字顶格写着:
“致最喜欢的你”
甜蜜的,温柔的。
这就是她称作垃圾的东西。
她曾经那些充盈柔软的少女心事,被他肆意践踏得残缺,变成了一文不值的废品。
是他亲手摧毁了这一切。
“云及月,”男人晦暗的瞳孔几乎在发抖,低声叫着她的名字,却像是在喃喃自语:“……原来这就叫报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