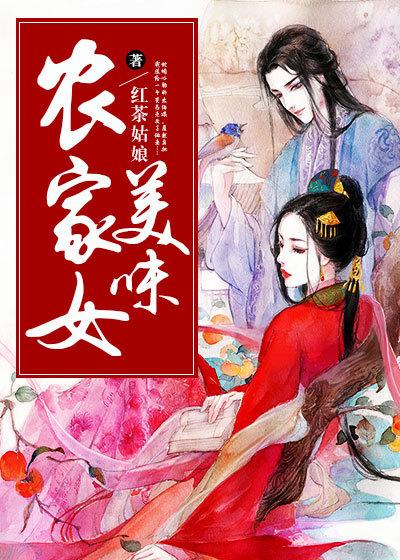书看迷>我见美人如名将 > 第155章(第2页)
第155章(第2页)
他本想将徐应白留在道观,由老观主照看,却不料徐应白最后钻了道观人手不足的空子,跟着他下了山。
十岁的小少年跟在自己师父身后,再一次看到了极其残忍的景象。
流民遍地,饿殍遍野已经是寻常。
野兽生食腐肉也不是什么稀奇事。
有一次,他们夜宿于一座破败不堪的庙宇,徐应白半夜被肉香味勾醒,揉着眼睛走到庙宇门口,看见几个骨瘦如柴的男女对着一口锅眼冒绿光。
旁边的野地荒草里面,静静地躺着两具干瘦且七零八落的尸体。
有一具甚至还是个三四岁大的孩子。
一股凉意爬上徐应白的后背,他感到一阵恶心,踉跄着退后,踩到了一根干枯的枝丫。
脆弱的木头在静谧的深夜发出震耳欲聋的咯吱声,那几个人猛地朝徐应白的方向看过来,浑浊的眼发出一阵亮光,仿佛看到了什么绝世美味。
周围死寂了一瞬,他们大喊着,疯了一般朝徐应白扑过来。然后下一刻,徐应白被玄清子狠狠拽回来,当机立断从破庙的一个缺口逃了出去。
奔逃途中,徐应白忍不住回过头,看见那几个人跪在地上嚎啕大哭,撕扯着自己身上的腐肉,吞进嘴里。
然而等到他们进了市镇,徐应白又见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景象。
他咬着嘴里面冷硬的馒头,看到对面的酒楼灯火辉煌,达官显贵坐着马车到那,极尽享乐之事,吃珍馐佳肴,听丝竹弦乐,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
酒楼的小二将一筷未动的粮食倒进泔水桶里面。
他们走了一个来回,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又从江夏郡回到了玄妙观,徐应白性子变得更加安静。
“师父,”他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玄清子重重叹了一口气:“师父……师父也不知道……”
两个人面对面沉默了好一会儿,徐应白抿了抿嘴,开口道:“师父,我想再去外面看看。”
玄清子闻言沉默着看徐应白。
十二岁,徐应白再次与玄清子出了道观。
这一次,他们漫无目的地在晋朝的疆域行走,他们去了江南,去了幽州,去了长安,他们远达嘉峪关,甚至还到了安西郡。
而到达嘉峪关的那一天,突厥骑兵骚扰百姓,一番混乱之下,徐应白和玄清子走散了。
徐应白只能一个人摸索着向前走去。
他身上的稍微值钱的东西都被人抢走,发簪,外衣,还有装着几十枚铜币的钱袋子都没能幸免,唯一一件留下的,是母亲留给他的玉佩。
行进路上,他会遇见一些路过的好心流民,分给他从沙地里挖出来的草根,无家可归的孤儿与他共饮一壶染着泥沙的、苦涩的水,见他衣衫单薄,几个人分别撕下自己身上的一块布,用麻草串在一起,给徐应白做外衣。
夜半时分,嘉峪关一带会变得很冷,有一次徐应白猝不及防地发了病,哆嗦着蜷缩在断壁残垣之下,睡在他身边,头发乱糟糟的乞丐婆婆解下自己脏兮兮但勉强算得上厚实的外衫,披在徐应白身上,抱着徐应白轻声地唱着西北这边陌生而又温暖的歌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