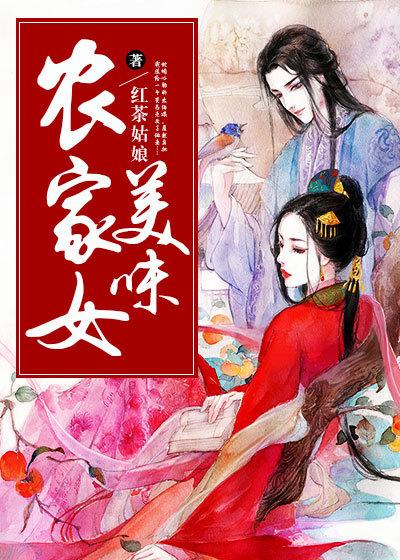书看迷>[综英美] 穿到哥谭后只想回家 > 第148章(第1页)
第148章(第1页)
苏西看见艾荣恩往红色电梯门的方向走,她又看了一圈,没发现别的出口通道,白房间里关押的实验体们对红色闪光和警鸣无动于衷。她刚才摸过禁闭间的探视窗,约有五公分厚的特制强化玻璃,不是她能在几分钟内打破解决的。
救火先救急。她看向身旁禁闭间里的蓝鸟,一边用小藤蔓甩开白大褂们,一边落回地面,用力敲打旁边的电子屏,凡是可按的键钮都按一遍,红色倒计时之下的波形图跳了几个高峰,屏幕上一些画着眼睛图案的标识渐渐暗了下来,等她再去看蓝鸟时,玻璃笼子里已空无一物。
一旁的白大褂群体躁动起来,或伸手或张臂欲拥,形成人墙拦截苏西的去路,而不远处的艾荣恩已经用密码打开了电梯门。苏西扶了下墙壁,用小藤蔓掀翻离她最近的几个白大褂,借墙壁作跳台跳起,踏过挡路的白大褂们的肩膀,在他们伸手抓她脚前先一步跃向下一个。
当离突围仅剩几排人,而他们都已经预先举起手做势要抓她时,小藤蔓猛地抽过去,像推倒多米诺骨牌一样推倒一片,苏西逮住空隙冲了过去,小藤蔓在手掌上绕了几圈,如直射而出的钩爪枪钩索,扒住逐渐合拢的电梯门,把自己甩进电梯。
她双手护头蜷着身体,重重撞上电梯厢壁,顾不上疼痛和撞击带来的恍惚,小藤蔓立马套狗一般套住艾荣恩的脖子,把他吊起摁在电梯门上,准备威胁他停下自毁程序。
然而电梯门并没有因为感应到人体而重新打开,反而似钢铁巨兽猛然咬合的牙齿,将艾荣恩落进电梯门缝间的手臂夹住,用力咬碎,发出一阵清脆的咀嚼脆骨的咔咯声,肌肉脉络崩裂溅出的残渣弄脏了电梯厢。
预料之外的发展让苏西几乎以为这不是电梯门而是某种处刑工具。
艾荣恩的手臂被电梯门死死咬着,苏西甚至没办法把他拉出来。她爬起来,不可置信地踹了踹电梯门,难以想象看起来普普通通的电梯也能成为杀人陷阱,但时间紧迫,她只能先压下心中的诧异,抓紧时间逼问解除自毁程序的办法。
“没有中断的方法”,身体的毁坏并不会让远程操控复制体的艾荣恩感到痛苦,他依旧平静着声线回复,“自上次病毒导致基地位置暴露后,各处基地都配备了严格的自毁机制。这座分基地内没有重要到不可取代的实验,只有一些消耗品而已。自毁程序启动后,唯一一处出口——也就是这里会被彻底封死,基地内部会被爆炸和强酸毁掉一切痕迹。”
“那里面的人——”
整个电梯猛烈摇晃一阵,往下坠了一段距离像是经历了强震,或者近在咫尺的大爆炸,灯光骤然熄灭,电梯内的应急照明灯随即亮起,幽幽绿色莹光挤满了闭塞狭小的金属盒子。
“零存活可能”,艾荣恩眼睛一眨不眨望着握紧拳头的苏西,“你明明有能力救他们,但你没做到,他们的死都该算在你头上。”
苏西强迫自己不要因内心被勾起的强烈愧疚自责而挪开视线,也不要因脑子里四处冲撞的愤怒暴躁而失去理智,她咬着牙,眉头低低压着,“不管怎么调整概率,在我看到的可能性里,即使阻止了爆炸强酸,你也会操控他们自裁,你把他们的死亡变成概率为一的确定事件,你才是凶手!”
“不,你有办法”,艾荣恩的声调毫无起伏,“你可以把别的世界线全员存活结局拿过来,可以选择那些不存在实验室的世界,直接抹除我们的存在。”
为了到达选中的现实和未来,世界会少量地修正过去。如果是直接改变既定事实,从那个时间点往后的世界线都会发生大幅度偏移。世界的自我修正本就是为了清除时间线中产生的谬论漏洞,更改过去更是逻辑悖论高发区。
就像祖母悖论一样,如果没有实验室,她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不会拥有能影响世界线的能力。如果目标是带回亡者的实验室不曾建立,要么是组建实验室的人不在了,要么是他们没有理由去建立实验室,他们的家人没有在非普通人的战斗中遇害,再或者,那个世界上本没有超出普通人的力量,才没有人会寄希望于死而复生。谁也不知道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苏西忍住大脑被Σ波干扰带来的刺痛,“但是我拒绝。”
被操控的复制体本身不会产生任何情绪,他只是用蒙上灰尘的玻璃球似的无神眼睛看过来,语气机械死板又满含恶意:
“是你拒绝提供帮助,你放弃了拯救基地里那些在几秒前还活着的人,因为你只限于自我满足的道德感让你吝于使用能力。就像你可以为了自己泛滥廉价的不忍懦弱,就无视世间降临的苦难,背叛我们去偏袒维护烂透了的世界。你拥有改变世界能力,本该为所有人带来幸福理想的世界,而你如此的自私伪善,是你放纵不幸毁掉无辜者的人生。”
好无耻卑鄙的说法。
“我究竟是上帝,救世主,还是你们的母亲?我就该对所有人的人生负责?我帮助他人只是在做我认为正确的事,不是我的义务,也非我的责任。我不是英雄主义者,没有弥赛□□结,不需要从拯救他人中获得满足。我对死者感到抱歉,是因为我知道社会道德如此,我努力做正确的事,所以我救人,我尽可能避免伤害他人,我严格遵守道德约束。你说我过去怎样怎样,呵,你还不知道,过去的苏西人格已经自我湮灭了,而我只是一个无根基的、凭空捏造出来的人格,我的一切都是被人为填充灌输的,性格、记忆、感情、道德标准都是创造我的过去之人希望我拥有的,严格来说我甚至不算人类,只是一个按照既定程序做事的虚拟人格。我当然会恨过去之人,但一想到这种情感也是在她为我塑造的思维模式下产生的,我又没那么恨她了。我怀疑我拥有的一切,事实上我一无所有。我一拍脑袋说‘过的轻松一点吧’然后就接受了这一切。这句话是谁说的?又是谁在在意这个?谁又想知道这些问题?于是我放弃思考这些没有结果的问题,但我没有放下,我只是忍着,一直一直忍着。直到你又把这些和过去之人有关的东西压到我身上。我不是她,我不想再重复一遍了,我不知道她和你们约定计划过什么,总之我不会代替她与你们合作,我也不在乎不足轻重的家伙对我的看法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