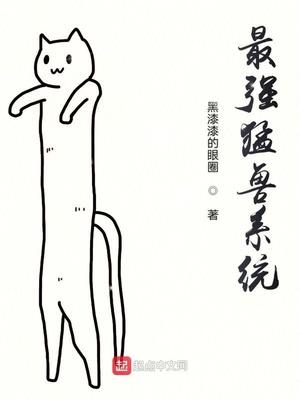书看迷>大唐小神探:开局被斩首怎么办? > 第511章 死者的身份(第1页)
第511章 死者的身份(第1页)
死者的宅子在越州其乐坊,看这建筑,是大户人家。崔梦真环顾一周,没发现有何奇特之处。“怎么不见鲜血啊?”沙刺史回答道:“因为被大雨洗刷干净了。”“大雨?”崔梦真惊了,“你们这里不是大旱吗?”李义琰轻轻扯他的衣角,小声说着:“你就盼不得别人好吗?”沙刺史解释:“越州确实连续大旱半年,不过早在五天前,便天降甘霖。”崔梦真负手踱步,沉声道:“不对,雨水洗刷绝对不会洗得这么干净,你骗谁?”“???”沙文石摸了摸胡子,经过这么一点拨,他也发现了诡异之处。“说实话,本官还是第一次来到案发现场。”李义琰觉得十分正常,毕竟一州刺史,不可能哪里发生了命案,他就要往哪里去。刺史是监督者,不是负责查案。要不是他们两个来了,沙文石绝对不可能踏入此处。“既然如此,那我们便随处看看吧。”两人在府邸内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沙文石已经离开了。“念鸿,你有发现什么端倪吗?”崔梦真沉吟道:“确实有,你看,即便地面上的血迹被人清洗干净,但是草丛中的泥土依旧残留。”鲜血入土,是很难处理的,除非你将整块土挖走,不然的话,肯定会染上红色。经过一番仔细的勘察,两人发现府邸内一共有九处血迹。李义琰轻声说道:“看这血土颜色相差无几,好像是同一时间染下的。”崔梦真却否定了他的说法:“你如何确定呢?要知道,只要是在一天内洒下的血,也会呈现同样的颜色。”“所以,你的意思是?”“我觉得,行凶之人,绝对不止一个!”崔梦真整个人都绽放出智慧的光芒。李义琰只是个典型的读书郎,他能把《唐律疏议》整本背下来,但是你要他查案,真是为难他了。两人搭配的时候,通常是崔梦真去推理,他负责评审,至于验尸,两个人都没学过。“我们回去府衙看看案宗吧。”案发现场没有什么新发现,估计有物证,早就被先前查过案的胥吏找到了。“居然死了五十多口人?”李义琰看着手里的卷宗,他微微愣神。这个数量的死者,可以称之为惊天大案了。而且,看死者的资料,他是越州著名的富商,身份可不一般。“越州首富?从事什么商业的?”负责接待两位大理寺卿的是越州长史伊兴文,他回答道:“死者张德业是做丝绸行业的。”丝绸?看这样的惨案,好像是仇杀的概率比较高啊,可是他一个卖丝绸的商人,怎么会与他人结仇呢?“你了解死者张德业的人际关系吗?”伊兴文点点头,看来越州府衙并非一群庸人,他们早已对案子有过深入的调查,只是一直找不到凶手。“张德业平日里深居大院,很少出门,就连邻居都没见过他几次。”“他在越州一共开了有十三间丝绸铺,生意很好,风评不错,可以算得上童叟无欺。”“除此之外,他的生意全是由他儿子。”就这?一个极少出门的富商,手下生意全权由他儿子张遥庐负责打理。“他只有一个儿子吗?”“一儿一女,均已过及冠之年(20岁)。”崔梦真愣住:“怎么孩子这么少?”伊兴文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大佬你是真的不懂还是假装不懂?李义琰开口解释道:“普通百姓不能纳妾,所以后代数量自然比不上士族。”“”崔梦真尴尬一笑。“那张德业的儿女们,都在这次事故中死了吗?”“女儿没有,他的女儿嫁到了扬州的郑家。”郑家?是那个大唐首富郑凤炽吗?伊兴文拜道:“是的。”看来,张家与郑家有姻亲,看来张德业的生意能越做做大,与他那个亲家有很大关系。众所周知,郑凤炽可是操控大唐绝大部分的丝绸产业。有这样的亲家,哪怕你是蠢货,都能在家里躺着数钱,更何况郑家在此之前的生意就做得不错。崔梦真却敏感的捕捉到一点,首富?越州首富。他问道:“请问张德业是从什么时候成为越州首富的?”“半年前。”成为首富之后,不久就死了全家,很难不让人怀疑,会不会是商业伙伴雇人行凶。在做生意的过程中,必定会惹下其他富商。越州丝绸业的蛋糕就这么大,张德业之所以能做大,必定吞食了其他人的份量。而被淘汰的商人,心里不服气,于是将他们全家给干掉了。到那时候,张氏丝绸铺群龙无首,缺少资金链,就会被其他富商吞并。崔梦真扬起下巴,对李义琰笑道:“忠坚(李义琰的字),你说我推理得对不对?”“有道理!”没想到,长史伊兴文很快就泼下了一盆冷水。“二位大理寺少卿,你们所想,其实我们府衙也调查过了。”“我们约谈过越州的所有丝绸富商,他们都矢口否决自己并未与张德业结仇。”崔梦真打断了他的话:“他们说没杀人,就是没杀人吗?哪个凶手会承认自己行凶?”伊兴文顿时哑言,话是这么说,但是你不能屈打成招吧?“可是,我们当时观察过他们的表情,并无发现有何异常啊?”崔梦真摆摆手说道:“你们不是专业的,自然看不出。”“这样,明天让他们过来找我,我一个个聊。”在大理寺工作七年,他审案无数,自认为已成为一名合格的神探。李义琰点点头,他与同伴分工合作。他去市井之中打探消息,崔梦真负责审理越州富商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