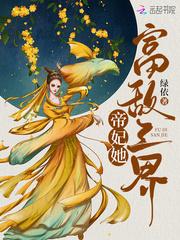书看迷>贞心淫骨绿意简 > 第11章(第2页)
第11章(第2页)
我不知该说什么了,绝色美女伤心欲绝的时候,鸟儿都没有力气扑闪翅膀了,我看着它们慢慢地消失在淡蓝色的霞蔚中,想着她唇齿留香的名字,心里悲伤卷席而来。
为什么都说一人一马,仗剑天涯?夫妻二人,就不好玩了……
长宁公主跟我来信,要我手书一幅《兰亭集序》。
我是在十二岁时第一次入宫面见皇帝陛下时,在一次非常私密的皇族家宴中认识长宁公主的。那年她十四岁。
那天见到的诸皇子皇侄有不少,他们彼此都很熟,皆第一次见我,想我必定是皇嗣血统,对我客气中又有疏离。
只有长宁公主和我聊得最多,她当是从圣上那里知晓了我的身世,年龄又和我相仿,向我絮叨个不停,倾诉着生活在王府和深宫内苑生活的乏味无趣,还问我习武之外,经史文章爱不爱看,喜不喜欢诗词。
我都含混点头,生怕自己说错了话。
之前未让我来的原因,长宁公主也代圣上向我做了转达:怕我年纪尚小,不像其他皇子皇侄一样天天学习仪注,不知进退,反而会被人轻视。
我说其实虽然我在武林之中,其实师父还是很注意教导我们为人处事的,说江湖也不全是打打杀杀,很多时候也是人情世故,慢慢地不再拘束,打开了话匣子,和她说了一些江湖见识。
她越听越有兴致,突然从怀里掏出一张纸,说自己写了一首诗,就是最后一句写不出来,看我能不能帮她:“身同流水净,心与白云轻。读史寒更彻,……”
这第三句的转折一下子把高度和难度提了上去,我倒是理解她的意思,在史书看到了人性,贪婪,阴谋……但怎么接,才能把这意思说到好的一面呢?
“衰荣笑古今,如何?”
这时我才刚看到第二遍,平仄、粘对、押韵还都没想明白,就已脱口而出,仿佛是冥冥之助有神灵相助!
这种神速的反应,把长宁公主震得瞠目结舌,片刻之后并转身向皇帝喊道:“皇上,我们皇家出了一个小诗圣呢……”
皇帝马上用严厉的眼神阻止了她。
当晚来未成年皇室贵女和皇族子弟有三十来号人,绝大多数都是蓝颜或平夫所出,皇帝的御座离我甚远,眼神却时不时地瞟向我,让我莫名紧张与惶恐,最担心自己这身衣裳打扮过于寒酸,不合仪注。
此后长宁公主就时不时将她在御书房珍藏的前朝诗集中发现的佳作手抄下来寄给我。
她一开始只和我交流一些诗词,有时她自己也写一点:“纺车轻转绕丝忙,炉火微红煮玉浆。庭前燕子飞来去,满心悠然待月光。小儿嬉笑绕膝行,却思夫婿对轩窗。手捧书卷静思语,笔端流淌是情长。”
然后请我指点。
我自己从来不翻诗词书籍的,怎么指点?只能回她一首诗:“绣余静坐发清思,煮茗添香事事宜。招得阶前小儿女,教拈针线教吟诗。”
以相同身份和同类场景相和,总算不失礼数。
她觉得我这首诗远她写的好:平仄相对工整,更有节奏感,语气也很流畅自然,简洁而富有生活气息。
她身份使然,慢慢地开始和我聊起了一些政治、社会、女性之类的话题。
皇帝与皇后常共议朝政,中侍省也因此成为连接后宫与前朝的重要纽带。
皇后通过中侍省向中书省传达特旨,涉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及三司的诸多事务。
中侍省虽不直接参与六部三司的日常运作,但其在女官选拔与考核上的决策和指导,时有透露出一些大政思路,隐约感到背后是皇帝本人的治国风范,朝廷施政时也会特别在意。
如此一来,中侍省不仅是皇家内务的管理机构,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朝廷权力结构中的重要一环。
皇后通过中侍省,既维系了后宫的秩序,又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朝政的决策。
朱漆案上玉尺金秤,量才亦量德。
青琐牖中鸾笺凤敕,录功亦录过。
自新宋改制以来,中侍省常以通晓文墨的嫔妃充任职事。
这些宫眷既掌内廷文牒,又常与省中郎官往来交涉。
因今上重绿风,皇后与诸妃常借此挑选合意的平夫、蓝颜,故此中侍省的官员遴选,尤重仪容风姿。
与长宁公主书信往来,言及诗词渐疏,更多提及的是女官铨选之事。
长宁公主时常就此垂询,言及慕容贵嫔这等大才女困守中侍省,领域相对较窄,委实屈才。
我虽然更想与长宁公主深谈榷场新政,看她信中偶有冗笔,每日还要耗费大半时间为三皇叔处理庶务琐碎,精力实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