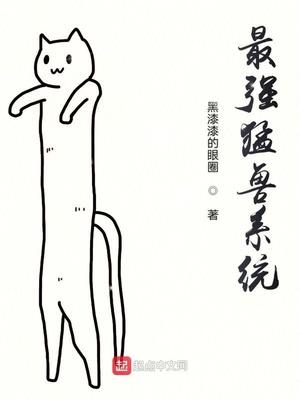书看迷>四爷怎么可能不做皇帝(清穿) > 第164章 第 164 章(第5页)
第164章 第 164 章(第5页)
从康熙四十七年到五十一年的这段时间里,康熙以一个大皇帝的睿智和果断,干脆地离开京城出巡各地方,不动声色地、冷静地观察着局势,思谋着对策。
老四胤禛在户部、工部办差。汇同老六、老九,老十二,老十三,甚至老十也去帮忙,甩开了膀子,放开手脚地大干。他们干得很好,超出他预想的好的百倍千倍的好!老四顺便也重用了几个深得信任的臣工,却都没有结党。即使是年羹尧,最终也是自己指婚年羹尧的妹妹,将年家绑在老四身上。
唯有人缘太好尚且年轻的老十三,要康熙始终认为,呆在老四身边早晚是一个隐患。
老十四这个“保姆”干的比胆小的老三好。别看他是八阿哥党。可是,一旦手中有了权,有了兵,他并不想听命于八阿哥:都是皇子阿哥,难道我就不能当皇上?明面上靠近老八,暗地里打着一个小算盘。这几年里,差使也办得很卖力,很认真。
唯一要康熙欣慰的是,他还是有点兄弟感情的,再算计,对他两个亲哥,也是顾着。
太子那,康熙看在眼里,自己都替太子急在心上。是,康熙是要利用他打压八阿哥党派。可康熙也没说,你就胡乱折腾一气,将自己人不管瞎的臭的都往朝堂塞吧?潜意识里,康熙还是对太子抱有一丝丝希望,证明自己亲手教导出来的皇太子,没有这么燥气用事。
康熙把任免官员、处理政务,甚至代皇上朱笔御批的权力,也索性给了太子。这下,太子可逮住机会了。他先是清理恩怨旧债,那真是点滴必报,从不手软。凡是他知道的,支持八阿哥的官员,一个不饶,全得想方设法打下去。接着,便是重新拉起来太子党,安插亲信。
八阿哥一伙的老十四管兵部,太子也意识到兵部重要。于是,便把自己的亲信、家奴,安排在兵部、京师和外边的军队中。可是,太子却犯了一个天大的错误,就是他低估了康熙的洞察力。康熙心如明镜却一言不发。太子奏一本,准一本。太子说用谁就用谁,你说贬谁就贬谁——朕倒要看看,朕到底养出来一个什么样的太子!看看你到底能做到哪一步?!
西部准格尔部落首先发难,派兵攻打西藏。军□□急,太子召集大臣和几位管事的兄弟来议事。按正常做法,这只是准格尔的小试探。而朝堂如果从内地调兵,万里迢迢地去西征,那可不是小事。粮响呀,兵器呀,马匹呀,军衣呀,怎么组织后方供给线呀,等等,等等,哪一件都不是一句话可以办成的。
可是太子先说他要亲征,见康熙不同意又大力举荐托合齐带兵,还给托合齐造势,拉拢老十二!
此刻,康熙和方苞在下棋,听说嵩祝等跟来的大臣们递牌子请见,方苞就要起身。康熙笑了一下说:
“李德全,你去告诉他门,且在大殿外头候着,朕待会儿再去。方苞,坐下,坐下。”
方苞不知康熙要说什么,又好似知道康熙要说什么,咽下一口唾沫,惶惶不安地坐下说:“请圣上训示。”
康熙沉思着说:“嗯——这件事,朕一直不敢说出来,因为话一出口,就泼水难收了。现在,朕不能不说了。方先生,如果今日有人要搞陈桥兵变,你以为他成功的把握有几分呢?”
方苞吓了一跳:“皇上为何这样说,大清太平盛世,焉有此事?”
康熙明白方苞的顾虑,宽容地一笑说:
“嗬……方先生,你不必吃惊,此事确有无疑。有人隐瞒了朕拒绝西部官员任命的批复,拉拢了密云大营和通州大营,又不经兵部,私自铸造了二十门红衣大炮,正对着承德山庄,要朕不能回京那。方先生,这事儿该怎么看?”
方苞想了一下说:“陛下适才所言之形势,草民万万没有想到。但据草民愚见,皇上无需担忧!因为大清当前的情形,与柴世宗的时候大不一样。大清的兵权都在皇上手里,大清不会出来“赵匡胤黄袍加身”。”
康熙点了点头:“好,方先生见高识远。可有人却利令智昏,这人还是朕的亲骨肉!”
方苞一听这话,马上就明白了,皇上指的是太子。他不敢多说,可又不能不说:
“皇上,请恕草民直言。既有这种事,就要当机立断,早做处置,免得事变一旦发生,不得不动用国法。汉武帝、唐太宗他们面对太子,都是悔恨心疼的呀。皇上,您不要等到那时候。到那时,皇上虽然仁慈,恐怕也难为两全了。”这番压在心口的话出来,方苞泪如雨下,起身一撩袍子,视死如归地跪趴在康熙的面前。
“皇上!”
傅尔丹、音图、隆科多、郭木布、李德全等人,一起跪下,眼含热泪哀求康熙。
康熙看他们一眼,忍住胸腔里翻涌的情感,痛心疾首:“朕宠着他,什么都给他。可是,如今他想要朕的命,难道朕也要拱手相送吗?朕给了他朕这颗脑袋,将来呀,谁还能护着他那?好了,这事今天先说到这儿,容朕再想一下。”
外头大殿里,意识到出大事的大臣们坐立不安地等着,一边等一边伸手摸着额头上的汗水。
里头的大臣太监们,一起跪在康熙的面前,一动不动地等着,听着康熙宛若受伤的困兽一般在寝殿里踱步,千层底的软缎拖鞋落在地砖上擦擦的声音。
朕宠着他,什么都给他。
可是,如今他想要朕的命,难道朕也要拱手相送吗?
朕给了他朕这颗脑袋,将来呀,谁还能护着他那?
康熙的每一句话,都要他们恨不得当聋子。可是又因为听到了,一颗心激荡着滔天巨量,脑袋里嗡嗡地响,什么也无法思考。
好一会儿,外头响起来熄灯的更鼓声,一声又一声。
康熙的脚步声停了下来。
“音图,刚刚朕的命令立即去执行。再命刑部和宗人府立即锁拿托合齐、齐世武、耿额等所有会饮名单上的人。……梁九功关押在景山。……齐世武的罪名,……朕记得,康熙四十六年,朕南巡,太子监国,当时是川陕总督的齐世武送来一封密折,这封密折竟然不是送给朕的,而是直接送到太子手里。”
康熙站在窗边,老去的眼睛幽幽深不可测地,望着承德秋天五彩斑斓的夜色,沧桑嘶哑伤痛的声音,缥缈的好似从天边传来。
“……这件事情,一直到康熙四十八年,八阿哥胤禩的人,弹劾齐世武,揭发出来。太子当年虽然监国,还没有使用密折的权力,齐世武当年作为封疆大吏,送错密折,把齐世武交大理寺议罪。托合齐,耿额等人,你们自己想罪名。另有太子安插在军中和各部衙门各地方的人,一个不漏的全部逮捕,押往刑部大牢,听候勘问!”最后一个“问”字里,都是凛然杀机!
“奴才遵旨!”
音图麻木地磕头行礼,面如寒霜,恭恭敬敬地行礼退下。
康熙面无表情,眼前好似是自己从先皇手里接过来皇位的那一刻,好似自己长大了,意识到自己只是奶娃娃皇帝没有一点实权,被迫迎娶赫舍里皇后大婚的那一天夜晚,打马跑在西苑的汗水淋淋,浑身湿透。
好似是赫舍里皇后临终望着自己和怀里的襁褓,目光万般不舍,苍白的嘴角的笑儿笑到一半就含笑而逝的模样。
“李德全出去传旨,按照计划,五天后启程回去。”康熙听到自己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