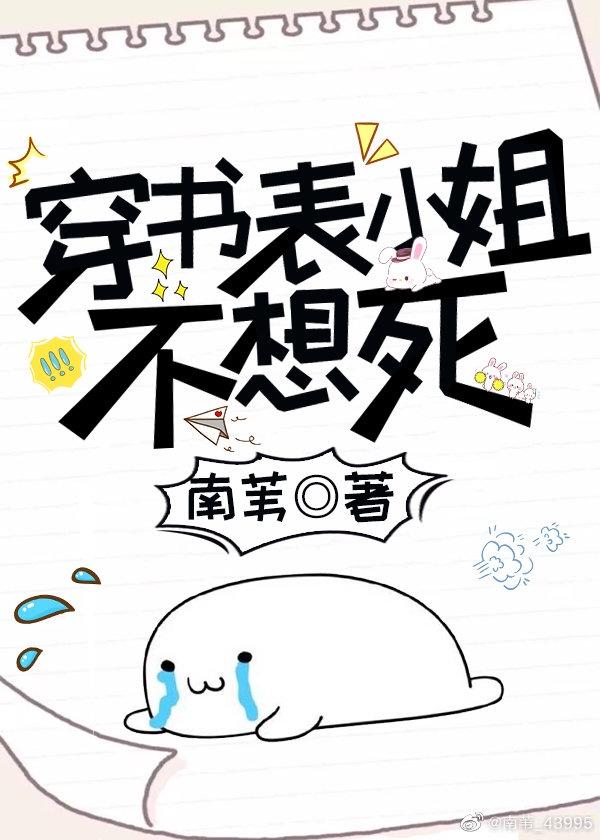书看迷>坏血 > 第 11 章(第5页)
第 11 章(第5页)
丁珂应都没应。
学姐一扭头就翻了个白眼。
学姐回到自己的地盘,身边都是自己的朋友,才找回自己的节奏。
朋友看着丁珂那边问:“怎么了?聊什么了脸色这么差?”
“没什么,等会儿暗示一下那几个学生,愿意玩儿的再带着玩儿,不愿意的就带着她们到舱内做保养什么的,尽量不露面。”
学姐说得同行不懂了,“怕什么?”
“不怕她们坏事,没钱没势成不了威胁。那个有点东西,不知道跟上边谁勾搭了,上去一趟毫发无损,还换身驴牌下来。”学姐烦得啧下嘴:“我跟上边没几个熟的,她要是多几句嘴,我他妈圈子别混、钱也别挣了。”
朋友不以为然:“夸张了。”
“你给他们送多少人,他们能因为一句挑唆就跟你掰了?”有人接着朋友的话说:“资历越深越怂了。”
学姐瞥他们一眼:“懂个屁你们,就那些少爷小姐把人玩儿了都不当回事,我们算什么东西。”
几人挨骂了不说话了。
有听话的表示:“行,等下我去问那几个学生,不愿意就不强迫。”
整个游艇最大的房间。
李暮近坐在沙发,双腿岔开,光脚踩着地毯,像是为平复情绪般一手拿梨一手拿刀地削皮,面前巨大屏幕是游艇监控,实时监测。
当然他只看丁珂。
复古音响在放一首蓝调风格的流行歌曲,女歌手声音跟丁珂很像。声线温柔,语速适中,好像纯白不光能形容她的长相,声音也可以。
除了这些可以看到的、听到的,她好像没一点过去痕迹了,可她若想重新开始,又为什么出现在他面前?
原本,她是谁不是很重要,为什么出现,出现干什么,有什么目的,他的兴趣一般。说是好奇,却也没真正探究。
那时最重要的是,她会再次成为他的谁。
可现在他想知道这些,只想知道。这甚至变成最重要的事。
他削完梨,没吃,放在盘上,微微歪头,手起刀落,梨变成两半、无数瓣。
手机响了。
他把刀子往桌上一扔,擦手布擦擦手,接通。
“喂阿暮,咋了?大半夜打电话。”
“你帮我去一趟津水。”
“干吗去?”
李暮近给对方发去一串地址,丁珂和丁卯户口本上记录的户籍地,然后说:“打听下两年前有没有发生火灾,出事的那家人家里都什么情况。”
“好。”对方没多问。
李暮近养的这群小孙子、好儿子,无论他什么时候用,他们都在,并且好用。他们只有一条生路,而这条路是李暮近给的,自然好用。人跟人之间掺杂感情会被感情左右决定,但若只有利益,就只有胜利。
束睿来了。
李暮近正好挂掉电话。
束睿坐到对面,看向巨型屏,视角一点都不偏,酒廊都没拍全景,丁珂却是全景,她还在正中间。
他收回眼,拿水果叉扎李暮近削的梨吃,随意瞥一眼,看到他脸、脖子挂的彩,一边嚼着一边说:“要不要打一针破伤风?”
李暮近没理他。
“这么烈,跟以前是真的像。”束睿一边说一边点头:“所以是,她像她,还是,她是她?”
丁珂从坐在酒廊吧台,喝的每一杯酒都是饮料。她只是说胃不爽,就连学姐和那俩男模请的,调酒师都换成了饮料。
刚才酒保是假意关心、真占便宜,调酒师不是,也不是谁打过招呼,是他认识丁珂的衣服。
自品牌推车给宋雅至送来,她一件没穿,却不影响品牌固定地送,她还为此专门腾出一间客舱放。
大概年消太多,所以有这个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