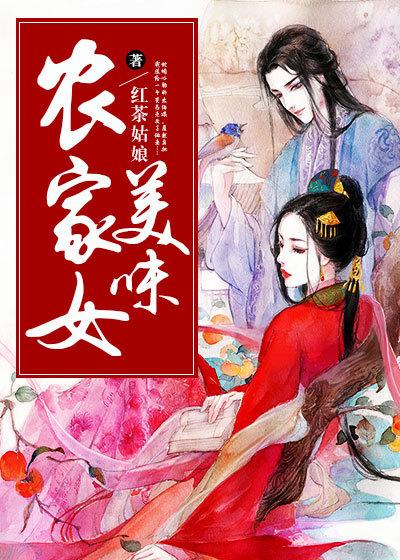书看迷>腰缠万贯从逃荒开始 > 第三百二十三章(第1页)
第三百二十三章(第1页)
后院的工棚是用来给雇工们杀兔子的地方,当时也是请的村里人用竹子简单搭建出来。
今天遭了无妄之灾,没顶住,直接废了。
当那群捕快们浩浩荡荡闯进永富村的时候,薛兴贵正吊着胳膊偷偷往床下溜。
薛兴贵在家躺了半天,外面诸事繁杂等着他处理,哪里能躺得下去?
薛兴贵自我感觉很良好,全身除了胳膊不能动,其他地方都好得很,头不疼眼不花,卧床一个月这不是折磨人嘛。
薛兴贵单手艰难地穿好鞋袜,蹑手蹑脚地往屋外走,不料刚打开房门就被薛米韬撞见了。
薛米韬这几日没去上学,家里人都忙得跟陀螺似的,就连大黄都忙着耕地呢,没人送他,又不放心让他自己去,便只能在家自学。
这不他学习之余还接了新任务,看着不老实的自家小叔。
薛米韬双手抱胸,跟看守犯人的衙役似的,小脸板的严肃,一本正经道:“阿爹出门前交代了,不让你出门,要你静养。”
薛兴贵气的弹他脑门:“你跟谁你啊你的,没大没小!你不好好看你的书,整天看着我干什么?”
薛米韬哼了一声躲开他的魔爪,迅速冲着院里大喊:“阿婆!小叔不听话,你快来!”
薛兴贵急得拿手捂他嘴,可惜已经迟了。
陈阿婆闻声而动,不过一眨眼就抵达了战场,既担忧又暗含谴责的看着薛兴贵,那眼神就跟薛兴富看调皮捣蛋的薛米韬似的,就
差明说你是大人了莫要耍小性子。
薛兴贵没脾气了,“阿婆,我保证绝不会碰着胳膊,就去兔厂看看情况,这不是新接了大单子,不盯着进度,万一交不出货可就麻烦了。”
陈阿婆正要说他满嘴歪理,突然听院门被人拍响了,她轻轻推了推薛兴贵,示意他莫要狡辩赶紧进去躺着,自己返身过去开门。
薛米韬像一尊小门神挡着不能出门的薛兴贵,傲娇的一扭头,留给薛兴贵一个圆滚滚的背影。
薛兴贵倍感头疼,蹲下身平视薛米韬,这小子都气他两天了,他当真是没明白哪里惹着他了?
“就因为我那天没去接你?”薛兴贵轻轻揪他的发髻,哄着道:“我那是有特殊情况,不是故意将你忘了。”
薛米韬眼睛跟着陈阿婆看向院外,背对着他嘴里哼哼唧唧的说:“你自己都不爱惜自己身体,我干嘛还要爱惜你?”
薛兴贵一怔,有些错愕的看着薛米韬的气鼓鼓的后脑勺,啼笑皆非道:“你现在倒是主意大,为这就跟我闹脾气啊?”
“阿姐说身体健康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是幸福的基础;先生也说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
薛米韬说完转头看着薛兴贵,两双如出一辙的杏仁眼默默对视着。
薛兴贵率先败下阵来,故意揉他的小脸:“行行行,你现在读了书,我都说不赢你了。小叔错了,行不行?”
薛米韬却还不肯
轻易原谅他:“病了也不说,家里人都跟着担心,这次好险没事,那下次呢?我就一个小叔,要是没了,谁赔给我?”
薛兴贵心情就像被春天的一缕阳光照进心中,暖意如潮水般涌动。
亲情诞生于血缘,血浓于水,却绝不止步于血缘,亲情可以如山,也可以如风,拂过无痕却又留下涟漪。